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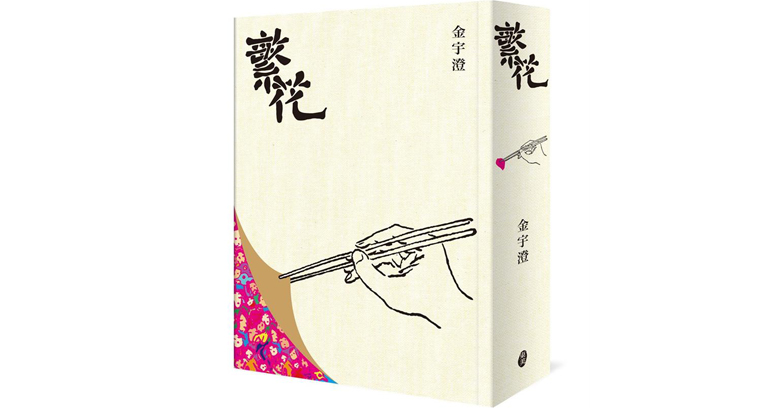
過去的好幾年,海派作家金宇澄的小說《繁花》成為藝文媒體的常客,無論是它所斬獲的書獎、文學獎,還是由它延伸出去的蘇州評彈、舞台劇、電視劇,常常被人談論、讚賞。除此之外,其謎語式的人物、敘事結構、所脫胎的網絡寫作、「一萬個好故事爭先啟後地起跑,衝向終點」等重要特質,在很長一段時間內都為人津津樂道。但無庸置疑,這部小說做的最好的部分,其實是它的語言。按照金宇澄本人的說法,《繁花》處於一種雙語的狀態:既保證中文讀者能夠順利地以普通話進行閱讀,又不妨礙滬語系統的讀者以滬語通讀全文。
這樣的效果,仰賴於金宇澄以滬語思維創作的努力。結合無數個歷史夾縫中的好故事,《繁花》綻放為一部真正的城市小說。我們甚至可以說,城市才是這部小說的主角。儘管小說的確有三位男性主人公——阿寶、滬生、小毛——貫徹始終,但他們和圍繞在他們的身邊的人,更像是編織上海的針腳,一種你方唱罷我登場的狀態,誤用巴赫金對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的評價來說,就是:不同的聲音唱著同一個題目。《繁花》的題目,就是上海。
外部人說起上海,想像未必很豐富,「摩登都市」是通常的描述。因此,讓很多人意料不到的是,上海其實也被稱為中國工人階級的發源地,而當時所謂的「蘇北人」,則是這一階級的主力。「蘇北」是江蘇北部多個地域的合稱,前者在十九、二十世紀遭遇無數天災人禍——如太平天國或者淮河改道,其治下的人民不得不顛沛流離,上海成為他們的目的地。
在過去,蘇北人和來自其他籍貫的赤貧人,基本上只能住上海條件惡劣的棚戶區:蘇州河畔、潭子灣,他們是上海精英團體的眼中釘肉中刺,是貧窮、落後、骯髒的代名詞,專門留給他們做的工種也侷限在拉黃包車、澡堂搓澡、理髮剃頭等低賤、卻又遍布上海的活上。
然而從《海上花列傳》以來,除了部分臉譜化的左翼文學,海派文學很少觸及這一塊,尤其是上世紀九○年代之後,當「懷舊」成為全球性的熱潮,人們在現代性的心緒中懷念往昔,難免溢美,也難免剔除不夠甜美的記憶。因此,《繁花》的不同,是它存在著不少紀錄毛時代(即毛澤東時代,1949~1976年)上海工人階級的生活區域——滬西大自鳴鐘、曹楊新村——的努力。從文學史的角度來看,這一努力起碼能夠達致兩個結果。首先,是我們終於擁有了另一種區別於「摩登都市」的方式來想像上海,金宇澄筆下的工人聚居地,不僅談不上時尚、先進,甚至相當逼仄、簡陋、鄙俗。連綿的瓦片之下,每一個房間都蝸居著四五口以上的人,工人早班晚班,投身於領袖偉大的現代化藍圖之中,空氣中充斥加工組的機床聲、蘇州河輪船汽笛聲,兼棉花廠、造紙廠中冒出的腐臭味道。
其次,是一度被左翼文學聖潔化的工人階級,在金宇澄筆下成為普通人。不妨以周而復《上海的早晨》作為對照,《上海的早晨》最早寫於一九五○年代初期,那時中國大陸民眾對未來都還相當樂觀、熱忱,周而復筆下的國家新主人——工人階級,與等待收編的資本家,呈現強烈的黑白對比。工人永遠聰明、勤勞、無私,對黨一片忠心,而資本家則向來卑鄙、愚蠢、心懷不軌,妄圖破壞革命。人的高下,由階級來賦值,而非自我的修行。《繁花》寫的卻是不太高明的工人,他們固然感到需要對領袖保持忠心,同時卻又難耐自我的慾望:對金錢、對飲食、對住宅,故而一肚皮「不響」的怨氣。兩本不同時代的小說,刻畫完全不同的工人生活,微妙地燭照著大陸民眾史觀的變遷,其實是很有趣的。
當然,《繁花》不僅寫毛時代的工人階級,也寫小資家庭、軍人家庭,如《海上花列傳》,所有的家庭皆精確到里弄,是一副真正的上海里弄索引圖。可惜這些描述基本止於毛時代,到了1980~1990的故事脈絡中,由於中國經濟起飛,條條弄堂漸凋零,座座高樓拔地起,小說主人公開始流連於一場又一場宴席,閒談不斷,桃色不斷:上海開始變味了。
有意思的是,我們是透過一個鴛鴦蝴蝶派的「情真」系統,看到作家對上海弄堂衰亡的哀悼。金宇澄從不否認他的語言與鴛鴦蝴蝶派的關係,但或許連他自己都沒意識到,他還依循了鴛鴦蝴蝶派的情感結構。讀鴛鴦蝴蝶派鼻祖吳趼人的小說,我們很容易看到吳趼人處處強調「情」字,在他眼中,情不限於風月,也關涉民族、家庭、朋友。但很顯然,由於鴛鴦蝴蝶派的言情性質,小說大抵都在描述男女之情,更精確而言,是女性的感情。藉由對「情」堅不可摧、感天憾地的渲染,吳趼人明目張膽地將其與「貞」扣在了一起,為貞節找到了現代化的合法途徑。《繁花》雖著力刻畫女性的性自由,但很顯然是不太贊成的,書中那些沒有來歷的女性(一如《海上花列傳》中沒有來歷的女性),無「情」無「貞」,總是妄圖以性資本奪取男性的經濟資本,又總是走投無路,下場淒涼。對比毛時代那些情真意切的鄰里美談,八○、九○年代的故事藉由對「情」與「貞」衰毀的書寫,成全其哀悼。
青春不再,真情不在,人生渺渺,歲月茫茫,無論發生過什麼,都要奔向毀滅,或者走入虛無——而虛無,是小說的基調。如小說的主人公們,自小由於特殊的歷史環境,導致命運無法自主,故而雖曾歷歷走過他們的童年、青少年、壯年,內心卻自始至終維持著等待被拆毀的狀態,像書中的姝華,在16歲那年被迫離開上海,去東北支援上山下鄉運動,異地的淒慘,令她發瘋。在真的瘋掉以前,她曾寫信回上海,告訴崇拜領袖的滬生:我們不必再聯繫了,年紀越長,越覺得孤獨,是正常的,獨立出生,獨立去死。人和人,無法相通,人間的佳惡情態,已經不值一笑,人生是一場荒涼的旅行。
對於拆毀無盡的城市而言,又何嘗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