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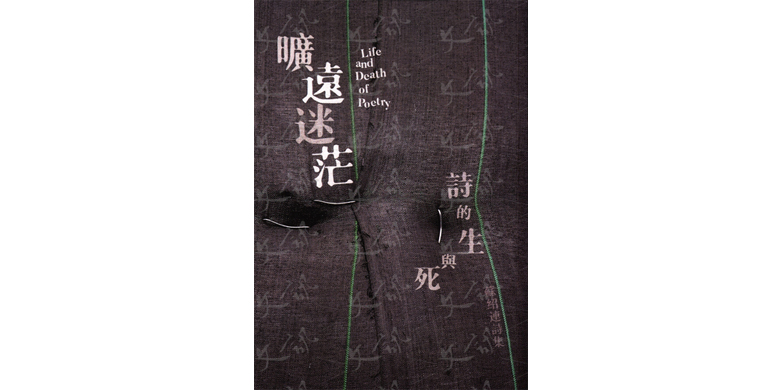
不少成名詩人在吟誦詩篇之外,為文抒發書寫心得與詩學主張,這類創作論名著,在台灣如楊牧的《一首詩的完成》、簡政珍的《詩心與詩學》,或在西方如波赫士的《波赫士談詩論藝》(This craft of verse)、里爾克(Rainer Maria Rilke, 1875-1926)的《給青年詩人的信》,或為書信,或為演講、或為散文,都可讓後學一窺創作的堂奧。蘇紹連也曾於2016年發表過一篇長文〈詩的生與死〉,闡釋創作理念,建構自身詩學,而緊接著在今(2021)年推出的詩集《曠遠迷茫》,顯然就承接了長文的觀念,以詩論詩,以詩評詩,講述了他特殊與犀利的詩學觀點。
《曠遠迷茫》一書分為上下兩輯,分別為「生之卷」與「死之卷」,上卷以詩學為主軸,討論詩的發生,詩人與自然、環境、政治與社會,詩的語言與意象,詩的發表,收束在詩心的純真。下卷則討論現代詩傳播系統的封閉,詩人相互取暖,加以面對文明的衰敗,蘇紹連逼問詩要如何跨過不同世代與社群?乃至詩可以跨越時空找到未來的讀者?以一本詩集提出諸多大哉問,不得不說相當具有雄心。
寫詩從來就不容易,賈島詩「三年得兩句,一吟雙淚流」,最為著稱,蘇紹連更認為詩應當從磨難與人生經驗中淬煉出,在序詩〈很容易就是詩人〉一詩中,以諷刺的筆法點出在網路時代,發表、宣洩與出名都變得容易:「很容易顛倒黑白\很容易用文字當子彈\很容易結黨營私\很容易找到診所\很容易自立山頭\很容易和上一個句子斷絕關係\很容易推翻\很容易就愛上了寫詩\無數的容易\人生如臉書\大家很容易就是詩人」,反而忘了詩的存在以及謙卑。詩的死亡不僅僅源於輕率,蘇紹連更指出詩社、學院、報刊、書店與政治都會成就「詩人」,也可能只是造就了模仿者、謊言家或是廣場上的擴音器。這首序詩點出了詩與社會和政治都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而蘇紹連在眾人爭逐詩壇領袖與雷聲閃電時,甚至不願意成為詩人,留下「你只想做一道彩虹」的雋語。
就詩的發生論言,蘇紹連相信詩是自身存在,而非人類去產生它,他主張:「『詩,先於人類而存在』,是人類後來才將它說出來、寫出來。詩,本來是無語言無文字的,在大自然中生發,以萬物的徵兆和形象而存在,根本是先在語言文字之前,也先於人類之前。」如是的觀點與鍾嶸的《詩品》序中所言:「氣之動物,物之感人,故搖蕩性情,形諸舞詠。」相呼應,詩原本就存在於天地之間,等待有緣人感受與觸動後,藉由詩人精熟的語言文字技巧,孕育為美好的詩篇。理解了蘇紹連的詩學觀念,閱讀〈暗夜裡的詩人〉一詩,詩人在暗夜裡寫下一個句子,是夢將句子在睡眠中安置在詩集中,顯然有超乎理性的力量在協助詩人書寫,詩末如是描述:
暗夜裡,詩人又獨自一人在睡眠中
打開詩集,把豆子灑成文字
前生的豆子
今世的文字
顯然蘇紹連提醒讀者和詩人們要敬重詩,因為詩的發生先於人類之前。而蘇紹連也期待詩人能不要懈怠,要勇於探索文字的奧義,寫出擲地有聲甚至驚天動地的詩篇,他在〈撐傘的詩人〉一詩中說:
當一名撐傘的詩人
必須一直朝天空誓死抵抗閃電
那一定是不懼危險的詩人
冒雨穿行文字間
終生寫著危險的詩
為不安的靈魂書寫,不畏懼一切高歌,是詩人的抱負,也成為詩人的志向。
蘇紹連也重視現代詩與中國抒情傳統的聯繫,〈詩人在遙遠的唐朝〉一詩中,來自唐代的詩人,要穿過薄霧的迷障,走到傳統不振的秋日午後。唐詩雖然只有寥寥數行,如同簡筆的仕女畫,能生動傳達情意與欲望,詩人感嘆:「哭泣的牆\吐出了蝶\詩裡複雜的傳統想像\才是愛」,而當詩人重返唐代,台灣的現代詩人則將以當代的觀點,「執行\再返回現代詩的程式」,充分顯現出蘇紹連從古典獲得飽滿的情意,在經典之前雖然有敬畏與尊崇,但絕不是屈從,在傳統的光照之下,要能以新的生命力創造出新詩。
在探究詩的發生與美好之後,蘇紹連則火力全開,對文明衰落、政治干預、流俗風潮連番的傷害,提出了「詩將死」的警訊,諷刺冷峻,讓人讀來笑中帶淚,如芒刺在背。
詩集題名同題詩〈曠遠迷茫〉中,蘇紹連援引了《大雅.召旻》的「居圉卒荒」,形容詩國滄桑,國土荒蕪,遍生榛莽,詩人只好反覆吟誦〈歸去來兮辭〉,讀者彷彿聽到陶淵明的哀嘆:「既自以心為形役,奚惆悵而獨悲?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實迷途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表露出文化國度充滿了困厄,江河日下,只能自力救濟,邊緣發聲,撰寫《邊陲詩家事略》與《詩典》,希望能夠為世界留下一批珍貴的聲音,也顯露出蘇紹連在絕望中的頑強,雖然在荒原中四顧茫然,但自詡:
成為深居的礦脈
不被發覺,我
只得點火
望著一顆心臟
冷靜的燃燒
類似絕境中抱有希望的描述,在〈詩人焚稿〉中:「這世紀裡有一詩人/從灰燼裡站起來/張開燒毀的/翅膀」,或如〈如果詩人成為標本〉中:「參觀者/凝視詩人標本/體內有月光/神,像琥珀/安頓了」,都不難發現雖然現代詩已經走進絕境,沒有讀者,蘇紹連呼籲:「詩人就相信詩的宿命吧,詩活不活得下去是詩自己的事,詩人唯有把詩寫好,將來能否被發現、能否被流傳,都不是詩人所能預料或是強求的。」(〈詩的生與死〉),因此詩人理應精心為未來的讀者奮起與燃燒,縱使稍成灰燼,縱令成為標本,也應展現天地所安頓的美好。
蘇紹連在《曠遠迷茫》中,同時也討論了「無意象詩」、「詩的音樂性」以及「詩人的素養」等主張,也批判創作環境中詩人為政治代言,語多直白,顯得過於急切,少了從容,如能把理論與批判融入後記的論文中,辯論析論,詩篇成為詩學主張的例證,相信以詩人成熟與多變的語言與技巧,應當能展現出更豐厚的「現代詩生死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