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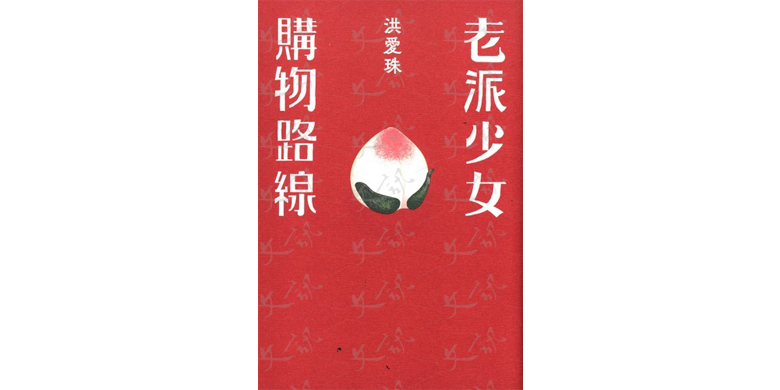
快一百年前,吳爾芙(Virginia Woolf)告訴了世界上的女人:「女性若要寫作,要有錢和自己的房間。」百年間,女性仍為此努力。而文學總比現實往前踏了一些,過往看似以男性作家為主場,煙火氣與文氣皆盛的廚房一地,近代也有女寫者將文與食都寫得豐神秀朗。從林文月、蔡珠兒、韓良露、王宣一到洪愛珠,她們多半不只識吃,也擅廚,更能寫。
洪愛珠出生於1983年,相對於精研寫食的上一代作家,她的不同先來自她如此年輕便熟廚事。廚事並不只是食事,翻開《老派少女購物路線》便知道,她循繼著外婆、母親的購物路線(更是心靈故鄉),從蘆洲本地市場到大稻埕、永樂市場、迪化街,已知買鮑參翅肚、椪餅綠豆糕、涼茶魯包了。能吃者眾,與洪愛珠年紀近者,也有許菁芳能記上一筆。而洪愛珠最大的不同,不只是她承繼而來的事物。比如那些讀來也想一見的老廚具,從烏心石鉆板到黑沉武刀,與那把母親留下的砂鍋,雖不來自什麼名窯場,卻能煮出好米飯(當然她也說了米始終才是最重要的)。或是巴黎廚具街揹回家的生鐵鍋,科普又好看地寫她如何沾冷油養鍋;京都名鋪「有次」裡,母親不買刀具或銅鍋,卻買了小小的「毛拔」,原來「小小毛拔,也見工藝高下」。當然,也少不了他們一家午後開長途車特意來到彰化花壇找黃有信老師父,買下的「黃銅冰勺」。這物與那物,順著書裡五輯的順序鋪開,「老派少女飲食與購物路線」、「粥麵粉飯」、「明亮的宴席」、「茶與茶食」、「南洋旅次」。她走遍本島、港島、東方與南洋,寫遍切仔麵、東西方乾麵與粥糜茶油,穿越那些冰勺與毛拔,種種如家族印記般識得之名與物,殊異拔秀的,卻經常是夾藏在美物美食間的其他。如那冰勺故事,其實是母親化療後,難得想驅車南下買的小物。
《老派少女購物路線》是從廚房開始的事,更是一部長長的台北本地家族史。洪愛珠本人的寫,也似一種悼亡,如她所寫,「時間是冰,不吭不響融化」。那些長街與宴席寫得熱騰氣派,百年家族當家主母外婆阿蘭的風華,講來已像傳說:「阿蘭結婚,遠嫁淡水河對岸,觀音山腳下的郊外之郊。形容自己進門時,足踏漆亮高跟鞋,一腳踩進屋內,鞋跟即深陷泥地,台北小姐的農村拚搏史自此開始。而老派淑女未曾放下往日講究。踏出房門,必全妝示人並抹朱紅唇膏,以馬甲束褲將自己紮緊,穿訂製洋裝,繫細黑皮帶。」卻都在時間的冰融後,滴落成一句:「我外婆沒有了。」寫外公的挑嘴與不好搞,吃粥粒米不進,只飲頂層米湯,到喜歡的老切仔麵店,一家三代坐滿店內,全靜待外公降旨「攏切來」的盛宴,也都散了。
最早看到洪愛珠的文章,應該是2018年的文學獎作品,她曾在訪問裡談寫作緣起,是在母親病期2014~2016年後才開始的,在那之前的她,甚至沒有寫作超過五百字文章的經驗。一如《老派少女購物路線》裡寫:「長長的百年的大街上,四顧僅餘我一人。」這本散文的不同,不在她將飲食寫至了多麼精巧與鮮活處,更在她以食憶人、以街尋人,像在油鍋冷下、麵店收攤後,以滿室油煙與水火蒸氣,祭拜至親離人。
洪愛珠的書名與習慣用字,或許都難免在讀後被冠以「老派」一詞。有賴李維菁作《老派約會之必要》,如今老派更顯時髦。談少女、也談老派,李維菁與洪愛珠卻也有些許相通,相通處是那比繁華更進一步的尋常模樣,理解並能操控時間的語言調度能力,因為堪破了些什麼奧祕,說出來的話總比旁人慧黠。但到底還是不同,即使心底皆為永恆少女,千萬少女,萬千模樣。若李維菁的字是放著收,像老母雞湯熬到濃白,底下那架一觸就與肉分離的白骨。那洪愛珠是收著放的,她雍容自在,面對時光也面對寫字,像是不留心間,雞湯上層結起的金膜。
因此,每個老派少女,都不是別的老派少女,洪愛珠的老派少女甚至不是單數,而是複數。是她、是母、更是外婆。在她心中,媽媽也是會創作的。「我認識我媽的時候,她早已是媽媽了。因此關於她的少女時代,須透過描述,和少數相片拼湊。模糊地知道,在她尚未被生活勞務及財務重擔,磨蝕成一個疲憊的中年婦人之前,她就是個珠玉般亮晶晶的聰明少女。」一如少女阿蘭,一如跨越三十後半的少女愛珠,因為青春永恆真空,如她所說,「永遠是每個女子心中的自由小鳥」。有些老派是蒼老,因為世道艱難蹉跎,而她的老派是源於繼承與記憶。就像病中母親,吃到她特地習來還原過往的食物時,和她有過的對話:「『這些,妳怎麼會?』我母親問。『學妳的。』女兒答。」
洪愛珠寫燉茶葉蛋,「先以筷子嗑破煮熟的蛋殼,色痕若要好看,手指捏筷尖上,筷頭往蛋殼彈擊,軟力中帶點巧勁,才敲出勻如青瓷上冰裂紋,乃可食用美。」她的字也大抵如此。力是巧勁,因此即使是裂紋缺口,也都像是青瓷冰裂、汝瓷開片,在〈為了明日的宴席〉一篇裡,全被寫得很美。因為弟弟的日本友人來訪,家裡設宴款待,是她母親生前最後的家宴。先從過往寫起,「通常在宴會前幾天,深夜裡見她伏在餐桌一角寫字畫圖。寫的是菜色排序和採買清單,畫的是擺盤的花樣。再將紙條貼在冰箱門上。每天看幾眼,有更佳方案,隨時調整筆記。」洪愛珠說看向母親的背影及神態,竟有寫作繪畫一般,創作的專注。縱使那般永恆真空如青鳥般的自己,連她也不識,「創作是什麼?」我媽媽她不講這個。她心裡沒有這個詞。然後,文章與記憶裡的母親,卻在宴席將啟前,「一人施施然步出廚房,進後花園。剪一朵重瓣茶花,點綴在几上。」至此,筆停在開席前,卻已寫到了席散。
這本書,是一冊購物路線,也是一次回望航道。是洪愛珠與母與外婆,三位一體的少女創作。創作是什麼?老派少女們以菜作答,有些創作在沒有字與廚房前,早已開始,還將繼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