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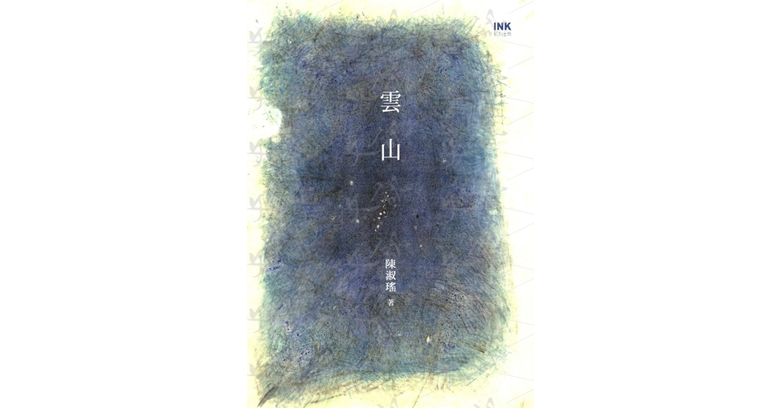
為什麼你們堅信只有幸福才對人有益呢?或許痛苦對人來說也一樣有益?
——杜斯妥也夫斯基《地下室手記》
一隻名叫海明威的貓,一對住在高樓的母女,一個夜半寫作的警衛,以及無窮無盡的山路。陳淑瑤十年寫出小說《雲山》,流水年華,瑣碎人生,日子無止盡地重複,初看還以為黃麗群小說〈卜算子〉母女加長版,我放棄比較快。後來小說家王定國提醒我越過40頁才漸入佳境,我囫圇拚上山頂,循著羊齒類植物一步一步下山,再次挑戰緩步蛇行上山,如是者三,才發現這小說好看極了。這七七四十九小節看似無所用意,內在結構卻很緊密,只要靜得下來(先請個七七四十九天假,就說最近咳了兩聲自主隔離了),漂浮在這無邊的文字海洋,隨它去,也不用小標題了,像楊吉永在山上轉悠,眺望遠方風景,站上各處木階石梯懸岩,三百六十度望遍環城群山,你突然發現封面那幅許國鈺2010年藍色油畫,如煙似雲,似霧非霧,標題就叫做「後勁很強的悲傷」。
這編輯天才啊﹗哏埋這麼深,沒跋涉完20萬字400頁還不曉得這一坨藍色是什麼。
讀《雲山》,好像無意間看到別人的行車記錄器,那麼多與我何干且伊於胡底的日常細節,簡直挑戰讀者耐心和腦補能力。這是本靜中有靜,慢還要更慢的《地下室手記》,起初你以為你永遠看不完了,卻在看完之後心甘情願再讀一次。像楊吉永看小說,掂在手裡,下意識比較已讀和未讀的書頁厚度,「感覺所剩無多,重量都落在一邊了……巴不得或捨不得讀完,早就心裡有數了。」我是這樣著了《雲山》的道以後,才領略到這可能是近年來我所遇到最魔性的一本書了。《雲山》至今得了不少獎,但我懷疑除了評審到底誰看完這書了?
和一般長篇小說的史詩宏圖不同,《雲山》全然不打算與外在世界掛勾一樣,它是3000片的巨幅拼圖,一個解散了的世界,一地碎渣。線索全靠讀者自己統整起來(是想逼死誰)。無愛天,無想天,夜歸人對上採蟬人。陳淑瑤這浮生千山路,春遲遲,燕子天涯,草萋萋,少年人老。表面靜定,內裡愛恨交織,人人肚裡埋藏著不能示人的祕密,隨著日子蔫萎了。總是在上山,上山,施烈桑或楊吉永,沒完沒了的長鏡頭與空鏡頭。作者以驚人的耐心織就一幅慢針刺繡的老後人生,地點是台北附近的郊山高樓,走到山徑上一樹櫻花閃閃灼灼,可和對樓陽台上的人打招呼,你在橋上看風景,看風景的人在樓上看你,像陰陽交界,夢遇見現實,也像正片與負片交疊的人生。
整部《雲山》,就像一個謎團,時間設定在一年半內,起首和結局都留給讀者去想像。末尾在火光餘燼之中,一切成空。蘇熊華遠望那曾經熟悉的大樓,楊家母女住的那層貼出待售字樣,夕陽金光閃耀,像美豔的火絨燃成一棵樹。屋內月曆停在四月。那「燕子樓空,佳人何在」的悵惘,如同胡蘭成再次一步步踩上張愛玲常德公寓六樓。那肉身與虔誠,全化成張愛玲筆下的感慨:「我一個人在黃昏的陽台上,驟然看到遠處的一個高樓,邊緣上附著一塊胭脂紅,還當是玻璃窗上落日的反光。再一看,卻是元宵的月亮,紅紅地升起來了。我想道:『這是亂世』」。
可不是亂世。《雲山》寫的,正是骨頭靜靜碎裂的聲音。
《雲山》裡,40歲未婚的楊吉永與母親繭居在山邊一棟高樓之上,二人皆心善,除了與勇哥小弟、余媽媽、美容院女老闆哲亮和樓下蘭心養護所外傭、清潔婦阿彌有些互動,二人離棄職場,似乎也經濟無虞,過著與人無涉的生活。言永前男友蘇熊華雖已結婚生女,仍偶來帶些吃食探望楊母。日日在山徑上走著的,有吉永、施烈桑、蘇熊華及其家人,還有諸多(如國標女、拐杖男與宏達一家子等)怪奇山友。
寒暑晴雨,四時流轉,這人間咫尺千山路,水悠悠,繁華已過。楊家人在女兒言永車禍猝逝後幾近崩潰。吉永後來的精神狀態,《雲山》始終以很隱諱的方式呈現,這也是全書另一謎團。畫作、心經、詩作與夢境交織,社區餿水桶上波浪板映出漩渦紋如梵谷〈星夜〉;黝暗地下室餵貓;山徑上巨石有外星人刻畫古文字;對門余媽媽家馬桶有血跡斑斑的鼠屍;超市雞蛋「白殼」看成「自殺」;山頂蓄水池方格想像成一個個骨灰罈;久違的大學室友鍾珊在一場搬家聚會中見了她回家哭到不行。
這樁樁件件,都說明吉永狀似優雅,從外人看來(包括萍水相逢因傘結緣的U先生),可不是這麼回事。《雲山》22節〈紅與白〉,與24節〈雨室〉裡吉永與前男友美術館偶遇,大量的畫作與心理幻覺交織,幾近夢遊,接近精神病患心理的寫照。人世如此美好,但吉永內心早已曝曬出焦味,像斑駁龜裂無法修補的「夏日街景」,也像一塊黃癟的裹屍布。她畏懼人,連蘇熊華來家都閉門不見,「走在路上就像個阿飄」,每周六出門爬山,常逛的還是夜間美術館,母親都心知肚明。
這山路上的少女,文筆好,潔癖加敏感體質(能預知姊姊的死亡記事),曾有美好家庭與藝術專業,父親近似美術教授或主管,母親應是中小學或鋼琴教師。吉永在父親病重時與同居男友陳為拓分手,搬回家中,父逝後照顧行動不便的母親,時而正常爬山,在美術館與植物園流連,時而在樓梯間或安養院崩潰大哭,無法正常與人建立關係。姐姐言永當年多才多藝,美如電影明星,一場車禍讓全家時間停格於相框中,父親去世更徹底擊垮吉永母女。
陳澄波畫作、木下靜涯的筆記本,山上拾得的蟬蛻或玻璃瓶中冰糖般的魚石,以及45節〈山雨〉父親雨中取傘,都是吉永對父親的思念。屬於楊母對大女兒言永的心碎,是38節〈浮木〉無意識彈著言永幼時彈的鋼琴曲;47節〈詩〉中,一本藍色筆記本,寫滿了楊母在女兒驟逝後回憶她一生的點點滴滴;49節〈餘燼〉中楊母送蘇熊華的兒歌〈悠悠札〉與雲南哈尼族的民歌光碟:「悠悠札,悠悠札,媽媽的寶寶睡覺吧……」、「閨女出嫁好時辰,未出嫁的安安心心啊,留家裡啊」。
內在心傷,外表靜默。《雲山》接近尾聲的47節〈詩〉中有一段描寫,細膩詮釋了一個心理創傷者美麗卻纖弱的內在世界:「霪雨浸泡葉子,葉肉腐蝕,殘餘骷髏白的葉脈纖維,她盡量照正常步伐前進,不刻意尋覓……小心翼翼以指尖推開服貼於路面的葉柄,慢慢撕離,像是自潰爛的皮膚上面抽去陷入其中的紗布。」
那紗布是父親和言永,這場戲的主心骨,卻從頭到尾缺席(類似《後宮甄嬛傳》的純元皇后),母親與吉永則是浩劫後的餘燼。楊母行動不便,吉永鬱症難解,外表看不出異狀的倆人,其實內在已然崩塌。45節〈山雨〉楊母跌傷與吉永浴室昏倒同時住院,加上之前10節〈周圍〉吉永驗出乳癌,《雲山》的結尾很可能母女倆人最終雙雙殞落,無一人存活。像《瑤草》的〈鏡子以及洗臉盆〉:「兩個一起粉身碎骨,沒有傷害任何人」。
《雲山》裡戲分很重的另一人是走路微跛,寫字像蠍子的施烈桑(諧音「撕裂傷」),也是整部書的穿針引線人賈雨村,甄事隱。這怪名字夜間警衛年輕靦腆,當過各式雜工,在好友小田的引薦下到這大樓任職,偶然結識楊家母女,結為莫逆。他常把習作給楊母看,與她同吃便當,共享生日蛋糕與心事。在他眼中楊家母女雖相互依存,早如大樹倒塌,神仙難救。38節〈浮木〉中,小施拿給楊母看的習作〈長夜筆記〉就寫到他上山時看見傾頹的大樹連根拔起,壓垮了坡下的相思樹與情侶樹,「葉子還綠著,做垂死的掙扎……她們一起被打進黑暗,墜入深淵」。那是樹木的撕裂傷,也正是母女下墜到深淵的寫照。
「兩個人的相伴,確確實實的相伴,是沒有自由的」。
《雲山》想要表達的,是日常即異常,瘋人與清醒的世界無異。而清與濁兩條稜線如此分明,社區女總監、蘇熊華一家(霏霏紋青千千)盡皆俗物,聒噪如滿山蟬鳴,楊家和施烈桑勇哥小弟則清澗入眼,山風徐徐。故事尾聲48節〈岩〉裡,勇哥小弟帶來葡萄,載母女倆遊車河,吃餐廳,歡樂一日遊,讀著竟有一種不祥。吉永與母親愈正常,就愈讓人想到張愛玲小說〈花凋〉裡的川嫦,趴在李媽身上像一個冷而白的大蜘蛛。「這花花世界充滿了各種愉快的東西……然而現在,她自己一寸一寸地死去了。碩大無朋的自身和這腐爛而美麗的世界,兩個屍首背對背拴在一起,你墜著我,我墜著你,往下沉。」
鼠疫之年,緩慢之書。流水雲山,人世綿長。《雲山》把痛失親人的無可痊癒與傷痛寫得極淡極隱,我喜歡陳淑瑤《花之器》裡寫貓:「入睡前自陽台往下看,一座座柔脊小島暗伏在庭院周邊。拋下這麼多錨,好像有什麼大風大浪要來,但是我的心情是非常寧靜的」。作者拋下了許多錨,那後勁很強的悲傷,棲息在風平浪靜的文字裡,給了讀者真正的寧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