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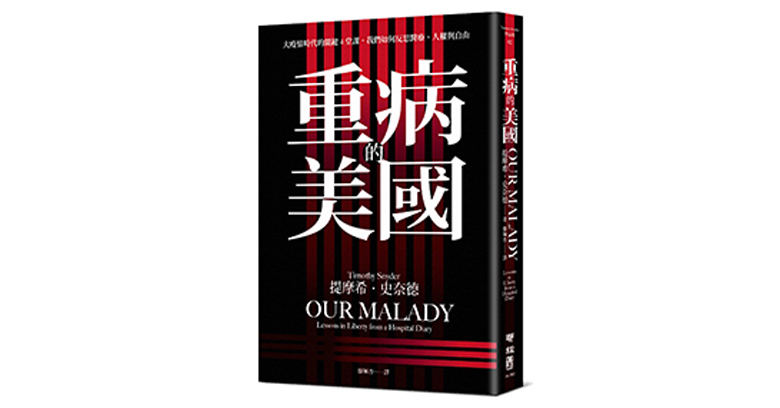
醫療照護是一種權利,而非一種特權。
——提摩希.史奈德
這本書講的是「逃出一個有缺陷的醫療系統的故事」。作者史奈德是耶魯大學歷史系講座教授,研究種族清洗、納粹大屠殺、蘇聯的恐怖統治,長久以來,他心中念茲在茲的是「如何抵禦過去的暴政」、「如何保障未來的自由」,2019年12月,他闌尾穿孔,然後切除,接著肝臟感染,又動了手術。病倒前,他在講台上講的是美國是怎麼成為自由國家的,住院後,病中體驗使他重新思考美國以及這個國家裡的自由。史奈德的病房日記,第一句話是:「這裡只有憤怒、孤獨的憤怒。」他發現美國聯邦政府和醫療的商業化使民眾不再健康,這也意味著疾病、恐懼使民眾失去了基本的自由。
史奈德急診入院,等待了很久,見到醫生的次數不多,見到了,對話也少,他感覺被診治得漫不經心,術後,因缺乏妥善照護而感染,出現敗血症,不得不再接受手術,史奈德在現實世界變成了旁觀者,他說:「我自身的不適是有意義的,它幫助我了解我們社會的『病』。」美國夢,大家耳熟能詳;美國病,我們不免陌生。
作者回憶多年前妻子在維也納生頭胎的時候,受到體貼的照護,享受了溫暖的福利,他的妻子在美國生第二胎時,經驗卻遠遜於前。奧地利的醫療系統既為孩子也為大人著想,美國則遵循著一個潛規則——「一切利益至上」。許多的人道對待出現在奧地利,美國卻辦不到,作者納悶。
2020年初,史奈德住院時,新冠疫情剛剛開始,整整兩個月,川普政府都虛擲在昏聵和誑語當中,新冠肺炎的確診案例則持續飆升。醫院沒有把篩檢放在優先,醫生對周遭的措施也沒有發言權,政府鼓勵製造商把口罩銷往中國,美國自己的醫護卻缺乏N95口罩可用,作者接受超音波檢查的時候,身旁未戴口罩的技術人員不斷咳嗽,大家膽戰心驚,許多醫生、護理師在沒有任何防備的狀況下染疫身亡,美國整體死亡人數更是超過了二戰。川普隱匿真相、操弄民眾,白宮爭論意識形態,而非流行病學,最終,威權主義威脅了國人的自由和生命。這場公共衛生危機暴露了美國民主的衰敗,大型媒體和新興社群媒體扼殺了地方新聞,社群媒體往往「消費事實,卻不生產事實」,民眾無法完整得知疫情真相。沒有知識,就無法健康,沒有健康,就無法自由,美國新冠肺炎的死亡人數躍上了全球之冠。
新冠疫情雪上加霜,許多美國人原本就沒保險,數百萬人隨疫情丟了工作,也丟了保險。疫情開始那幾周,兩千多萬美國人失業,而美國億萬富翁的財富總數卻激增了兩千八百二十億美金。美國,財團老闆一向是眾人的榜樣,即使危在旦夕,大眾仍然整天做著變成超級富豪的白日夢。
美國的醫療產業是一種寡頭壟斷,極度商業化之下,人不是上帝的孩子,而是利潤的來源,財富的分配狀況決定了一個人能受到的醫療照護,美國人在這方面付出的遠比其他國家的人多,得到的卻少。史奈德發現美國的醫療商品化造就出了海耶克(Friedrich von Hayek)《通往奴役之路》裡說的「被剝奪權利的中產階級」。史奈德認為美國應該建立「單一保險人制度」,而非向私人保險傾斜——讀到這裡,不禁為台灣人慶幸,也更瞭解為什麼那麼多旅美台人返鄉健檢、治病。美國的公共衛生系統嚴重失靈,史奈德認為醫療系統應給醫生更大的施展空間,讓他們的用專業去設計一個系統,使所有美國人都有健保、得到應有的照顧。醫生具有科學專業和人文素養,當民眾需要醫療時,應該想到他們,而不是「躲在他們廣告形象背後的公司」。
《重病的美國》從作者住院時開始寫起,當時,他「對人生最終要面對的那份孤獨感到憤怒」,他漸漸痊癒,卻仍感憤怒,不僅僅為了自己,更為了所有的美國人。他深信人人都應享有健康照護的權利,那是人「變得更自由的前提」。過去,我們很少在公共框架中思考自由與健康的關係,作者說的沒錯,健康是自由的前提,平時,基本醫療照護制度為公民提供了安全感,一旦有了需要,公民能得到及時、妥善的基本援助,社會整體方能真正安穩。書中不只一次提到了「自由的悖論」,作者說:「沒有別人的幫助,我們就無法做自己;沒有與其他人一起建立的連結,我們就無法獨立成長。當所有人都看得見真實的世界,才更理解為什麼要做某些事,讓我們無論是獨自一人還是與他人在一起都生活得很好。」以中國傳統思想的角度去看,重視個人的道家與強調群體的儒家,兩者在當代是可以調和、互補的,每個個體都該受到尊重,其組成的共同體既不應任人自生自滅,也不應藉由感情勒索而令其彼此牽制。「人」與「仁」原本即是相互涵攝的,適合個體生存和發展的群體應把設身處地、將心比心的原則轉化為專業取向的客觀制度,而不是取決於財富多寡的優勝劣敗原則。
史奈德在書的〈尾聲〉寫道:「無論我們生活在這個國家的什麼地方,無論我們生什麼病,我們都不是物品,而是人。」並說:「我們要把彼此當人看,才能發展得更好。」有夢最美,世人對「美國夢」往往過度美化了,從對民眾的醫療保障去看,竟然成了夢魘,《重病的美國》即是史奈德在夢醒時分的現身說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