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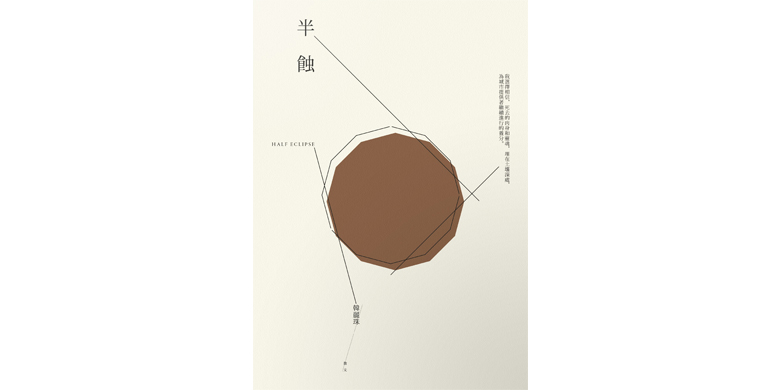
「沒有根而生活,是需要勇氣的,一本小說的扉頁上寫著這麼的一句話。在浮城生活,需要的不僅僅是勇氣,還要靠意志和信心。」西西1986年寫下《浮城誌異》,雖娓娓誌異,卻沉沉壓著在「時間零」等待「時間一」的鬱悶,而且懸於半空的奇異,早已變成時時仰望天空卻無法飛翔的日常。
到了2021年,面對大清算、大瘟疫的香港人,曾經企圖起飛的浮城人,結果被硬生生折斷哪怕只是夢中偷長出來的翅膀,帶血下墜。韓麗珠在《半蝕》裡斷言:「浮在空中的城,早已掉到海裡。每天都有人自欺欺人地說,這裡仍然繁榮安全。每天都有人呼救,卻彷彿被困在一個噩夢那樣,張大嘴巴,發不出任何聲音。」
傷痛、消失、流離,海是香港人的苦,一片苦海。沒有乾乾淨淨、一了百了的屠戮,只有緩慢的沒頂,只差誰還未淹沒。《半蝕》是這樣的一部痛之書,悟之書,擁抱著一種渾身帶刺、揭破虛妄的執著,同時捏著自己懼怕的柔弱心臟,因此更重要的,也是一部真誠的惶然之書。韓麗珠與更多落水者一起,不得不掙扎,茫然四顧,然而也盡力沉靜下來,感受周圍的水流,持續地思慮並訴說,寄望著彼此能在接續而來的打擊與磨折面前,好好與傷患共處,承擔自身生存的重量,既然我們已抵達黑暗。
★「更深刻地活著」:洞穴裡的修行日記
疫情開始,時針彷彿撥回零。政權以防疫為由限制人身自由,乘機追究抗爭者,人心的黑暗被牽引,滿溢般傾出,不僅是掌權者的凶暴,被壓制者的噤聲、封閉與種種習以為常的惰性,也可能成為幫凶。但當中,自有無奈的必然。韓麗珠說,當城市的欄柵愈來愈多,沒有人不身處欄柵和欄柵之間,自會有人為著還能順著欄柵指引的路而安心,但另一端是深陷欄柵的萬劫不復者,在痛苦的盡頭,因為被碾磨成粉末,歸於我城的地土而滿足。於是,蝕沒有全蝕,侵蝕破碎的開端,也是光芒湧出的缺口,死死生生,個體的自由與奉獻,是小循環,一個集體的沉淪與療癒,是大的轉化,中間必經磨蝕,但進入磨蝕,進入那個盼望與絕望的「現場」,起碼在推動蝕的輪轉:「『現場』已經從一個具體的空間,成了一種意識型態。」
韓麗珠感受著「蝕」,也更深刻地感受著「半」。整本書就像一趟辯證的旅程,所照明的無非是情感的掙扎。例如說到「現實」「真實」之辨,「現實是組成花崗岩的礦物顆粒,真實則是花崗岩本身。」真實本來難以面對,無法理解,但一重重痛苦的逆境,迫使我們面對,甚至置身其中,原本的虛妄生活反而有機會被撕開,如此推到「囚」「口」之辨,「口」的困鎖愈發顯得不可免,惡法之下,每人都可能成為階下囚,而真正試過地獄的人,反而能單純地相信有出口,出口有光。
你可以說這種辯證的追索,這種半蝕式的心悸微光,是應付創傷的某種防禦機制,但事實上也沒有這麼細膩、親密而富身體性的機制。書中示範著的,無非是更誠實敏銳地活得像人,更接近真實,而非僅僅順應現實,因此也不致無知覺於極權的碾壓,不致無聲地在碾壓下消失。
日常不常,韓麗珠剖白從疫情到國安法實施以來在日常與無常間擺盪的生活,細節歷歷,專注坦然,如修行日記。防疫時期的獨處在家就像身心的穴居,停滯的同時也可以聆聽自己。過去的傷口會說話,窗外的景色會說話,甚至反過來觀看你。管制無處不在,誰不被觀看?但除了更敏感地覺察到,暴政不會放過每一個獨立的個體,深居簡出時,恐懼籠罩時,也能更敏感於一絲縫隙送來的陽光,一縷飲食的香氣,呼吸與心跳的流向,以至願望的遺骸或不可能。比如說,一段關係,曾經深刻,卻終於變成侵蝕,猶如共同飼育的牛,漸漸被餓死,牛的眼睛如湖泊,可以喝到清澈的水,最終只能一任乾涸。比如愛,像亡貓重臨,只能一再臣服,把香港人無私的犧牲、代價,和個人的創傷經驗連結,是更痛切的體悟。
在虛妄的第一人稱和難以抵達的第三人稱之間,或許要先承受第二人稱在痛苦中來臨,並當成修煉,承認內在的空洞以及失去已經成形如獸,讓自身成為他者。韓麗珠不啻在編織著另一種洞穴寓言,這洞穴雖然隔開,也是容讓療癒和轉化的異質空間,不需要機器、投映,洞穴就是感官,與自身的黑暗臍帶相連,最後也不是為了離洞外出,不是為了光,而是擴展那黑暗。能灌漑生機的水流,就在你願意張開、深入的時刻。
韓麗珠在法院旁聽年輕抗爭者的審訊,自覺到在這痛苦的時代,不離開,並作不同的堅持,其實就是「更深刻地活著」的時機。愈來愈徒具外殼的法庭不也是一種洞穴嗎?漫長的審訊能把人的意志和信心壓垮,也在考驗生而為人的延展性,讓我們感知、觀照軟弱或柔韌的命運。每個人都有時間零和時間一,真正活著的人走進中間的峭壁。
★創造一個他者
但韓麗珠以柔靭的書寫展示出來的,並不是單純對時間的信仰。與其說她相信活著,不如說她相信創造,意象紛紜的書寫就像黑暗而沃饒的容器,吸納現實並呼喚真實,從而體現了創造作為一種深刻的活法。日用飲食的經營是創造,為抽象的信念冒生命之險、主動投向死,是創造,和自己對話,也需要創造力。創造指向的是生而為人,面向殘缺以至虛無的尊嚴:「牢房的存在是為了剝奪人的自由,可是人的創造力在於,在被禁制和壓迫的環境裡,盡其所能,活得像一個人。有人讀書,有人寫作,有人運動強健身體,有人自習語文,利用限制,保住作為人的尊嚴。」
韓麗珠提及寫作,對她來說就是由尋找敘述聲音,到被敘述聲音找到,如魂魄到臨的過程。書寫是如此親密的行為,讓我們不得不接受種種淪陷失落,繼而找回在暗處靜靜療傷的自己,或成為殘缺的他者,最終,可能有一個世界形成,足以承載傾吐,安放死結。但以什麼方式尋索、承載?以重新界定現實的方式。對韓麗珠而言,很重要的就是空間的重新界定。從防疫時期的穴居,到記憶的耳蝸(「居住在每個人的耳蝸內,都有一頭容易受傷,或早已傷痕纍纍的動物。內耳是個低窪地,不容易有風經過,吹散聲音的雜質」),從遷徙的生涯中對房子如生靈的體悟,到房子裡那一根為了營造安居之地的繩子(「於是,我在原地站立了很久,觀察那根繩子的遺骸,當繩子失去兩人所創造出來的緊繃,只能回到一種崩潰的狀態,很像一尾已失去生命的蛇。」)韓麗珠都在跋涉,在幢幢影子與聲音中,走向所謂家的背面,那一層一層從體內、從歸屬的土地貫穿到更黑暗處的,人性的根。
因此《半蝕》依然不可能是療癒之書。除了不相信有所謂癒合,也因為書首先就是內在之書,因為書寫就是基於癒合的不可能。「每個人所看到的世界都是一本書」,而每本書又是迥異的世界,遇到的事,相當於便利貼,傷患則是便利貼的相反──把書頁和書頁封起。2019年以來的香港人,彼此的書開始接通,甚至共享便利貼,而當封印的書頁不得不撕開,向天索解,痛楚便「溢出了語言的邊界」。然而,《半蝕》畢竟不只是無語地把痛狀攤開,創傷在書中更成為繫連的線索,引導著包括作者在內的惶然者,尋找著創傷更多可能的形狀:小至裂縫,大至深淵,腹中親密凶險的獸,陰影密林,或一株把我們的樣貌與生命改變,同時沉默地茁長的奇異植物。
★活成一本惶然之書
「只有頑強得近乎天真的人才能相信,種子正在泥土裡蠢蠢欲動」,那麼,這樣天真的人還有沒有?韓麗珠以頑強的書寫,確認著。如果我們必須接受自身作為千瘡百孔的他者,我們也可以相信,有那麼一個天真的自己,能夠在頹垣敗瓦中,抱著微小的生存意志活下去,相信我們自身就足以活成一本書,寫給那個天真的自己。
也許我們都經歷過像「我停留在那裡,快要到達一輩子」的恐怖時刻,猶如香港經歷過的無數個彷彿無盡的長夜,和當下面臨的囚禁。我們只能泅渡,「沿著恐怖一直走,走到慈悲」,每個人都有自己從時間零到時間一的路,無人能代你經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