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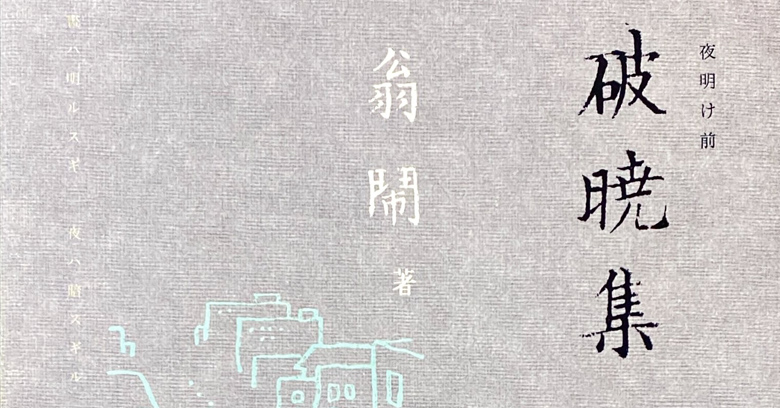
我想戀愛,一心一意只想戀愛。為了愛情,叫我獻出此身最后一滴血、最後一塊肉也在所不辭,因為我相信只有愛情才是令我的身體與精神完足的唯一軌跡——我偏不說是奇蹟,正是軌跡,因為只有它——只有愛情才能滿足我所祈求的每一個點上的條件,連成全宇宙唯一的一條線——從這個意義上看的話,說奇蹟倒也無妨跟妳說這些故事之前我得先聲明,請妳干萬要記 得我是一個混跡在千萬人當中也不會特别突出的、再平凡不過的人了。現在,就讓我把自己的經歷和想法不誇大也不扭曲地通通告訴妳。
不知道對妳或別人來說如何,至少對我而言,愛情的開頭多半慘痛不已。
有一次,對,大概是十歲左右的時候,我在鄉下的家中看見庭院裡一隻大紅雞冠、雄糾糾的公雞突然張開了一邊的翅膀,用爪子用力撥著院子裡的土。牠維持著同樣的姿勢,緩緩地向院子裡一雙平和地啄著土的白色母雞靠近——我不是出於好奇所以從頭看到尾的,那個光景就這麼偶然地扎進了我的眼膜,但這不是重點——公雞彷彿要證明自己的雄風一般,一步一步地往母雞身旁磨蹭;牠的雞冠直挺挺地立著,顏色更紅了,就好像身體裡的血液瞬間飽脹。你可知道,在那樣
的時候,不只是雞,連看著的人都會感到熱血沸騰啊!你別笑!千萬別當頑笑!因為我是一本正經在告訴你這些事的。至於那隻母雞,母雞只是溫順地縮著身體閃閃躲躲;實際上,當那隻公雞電光石火般地猛咬住她的脖子、想跳到她身上去時,她逃走了。她為什麼逃走?還能為了什麼, 不就是因為她不能開口說不,所以用行動表示的嗎!這麼一來,公雞更加兇暴了,牠像一枝箭直直地往母雞的後頭追去,又以加倍猛烈的動作跳上了母雞的背,像顆子彈般穩穩地嵌在她的身 上。結果如何呢,前一刻還要逃跑的母雞突然放棄抵抗,竟然就將身體弓起來了。接下來發生的事就不提了,也沒有說明的必要了。我突然想,就是這個!就是這個瞬間!人類三不五時地奔波勞碌——說得更白一點,大家整天戴著一副聖人君子的面孔又是買股票,又是生意、又是公司云云地總是轉個不停的原因,想必是預想到了這一瞬間的歡愉,才能那樣義無反顧地汲汲營營吧!你說這想法太乖張?一點也不錯,我就是這樣一個乏味的男子,不過我只是遵守最初和你的約定,
把所有的事情原原本本、不假修飾地說出來罷了。我再怎麽笨,也料想得到你在聽我說這些故事之後只會更加確認我是個乖張的人。但是,你要怎麼看我,那是你的自由,完完全全是你的自由,不是嗎?你難道甘心像個呆頭鵝似地讓我干涉你的想法、隨意操縱你的思想嗎?你問我到底在想什麼?不,我沒有什麼了不起的意志,更何況我還有凡事務先尊重别人意向的癖性。雖然自己說來都覺得丟人,但請你相信,我實在是因為太尊重别人的意志,到頭來讓自己連意志這東西也失去了。我願意告訴你這意志喪失的經過,但恐怕開了頭會沒完沒了,所以我還是快往下講吧!不過話又說回來,從我這樣跟你說話便可以知道,我並不算全然喪失意志。這不是笑話。再怎麼說,人總不至於在意志全失的狀態底下還能生存,
所以,請你明白像我這樣的人也還殘留著一小片意志,這就夠了。
再回頭說雞的故事吧。牠在我的身體裡種下可怕的思想後,又若無其事地用爪子撥著院子裡的的土。說實話,在那之前我還以為嬰兒就像父母親說的那樣是從石縫或頭頂上冒出來的,但我已經知道那沒有道理了。從此以後便持續了一段漫長的暗中摸索,暗中摸索的結果想必你也看出來了,意外一反常態地過早為我帶來了一線光明。你知道香蕉吧?把香蕉放著不管當然也會熟,不過若是想讓它早點成熟,就要每天把它從甕裡拿出來曬太陽,或者把香插在甕裡,這就叫催熟。一經催熟,原來要三週才能熟成的東西只消一週左右就成了。三週和一週,這可是相當驚人的差別呢!我也同樣地在少年時期經歷了反覆不斷的催熟再催熟,因而不由自主地造就出我的老成。這世間若說有哪個少年比我更老成,我是不信的。
在那個犯忌諱的事件之後,我又目睹過不知多少類似的光景。是的,我永遠記得自己十三歲的那年春天,因為順利考上中學,和家母一起往山上去向某一個非常靈驗的神明那裡還願。拜過神明之後,我獨自走到廟埕上。那裡是一片南風習習、春色駘蕩的景致——真只能這麼說了,除了說春天以外沒有别的詞彙可以形容。你問我的出生地?忘了告訴你,我出生在南方的國度。你說你是從北方的雪國來的吧!如果有一天你厭倦了這個都市的生活,想要找個風光明媚的地方去走走,不妨去看看那間廟所在的地方。我站在廟的廟埕上,突然看見兩隻鵝搖搖晃晃地從我的眼前走過,我馬上想到這兩隻鵝一定是一公一母,若非如此絕不可能那麽親熱地走在一起;是的,如果不是一公一母的話,走在一起不可能看起來那麼親睦。接下來的發展就驗證了我的判斷是對的。兩人,不,是兩雙鵝走到了屋簷底下,其中一隻用喙啣住了另一隻的頸子,被啣著的那隻十分温順地蹲了下來,另一雙就跳到牠的背上去。可是這傢伙不只體型大,還相當笨拙,眼看牠的腳一再打滑,一遍又一遍地從母鵝背上滑落下來。你猜牠摔了幾次?當我發覺應該從一開始就計算的時候,已經數不清牠掉下來多少次了,光是我從半途起算的次數,他就跌了十九次左右。真是驚人哪!到最後讓看的人都不免為牠著急起來。不過,那光景並不會讓人感覺不舒服,因為那兩隻鵝都流著口水,是真的在流口水,還有………
還有,可以對你說說更加如癡如醉的那對蝶的故事。那是我中學二年級快要結束、正是十五歲那年的早春,某一天,我正在音樂室彈鋼琴,有一隻翅膀豔麗的鳳蝶從開著的窗戶飛進來,不知怎麼的就掉到了我手指前的鍵盤上。正想用手揮開的時候,我猛然發現那不是一隻,趕緊把手縮了回來。沒錯,那是兩隻蝶像被釘牢了一般、緊緊地黏在一起。這兩隻蝶宛如人酩酊大醉時那樣,晃晃悠悠地顫抖。在那一瞬間,暴虐取代憐憫占據了我的心。我這個人,請聽清楚,從少年時代要過渡到青年的那段時間實在是沒什麼慈悲心腸的,簡直可以用狂暴來形容,能破壞的東西全破壞光了,因為那時,違背我自身意志的另外一個意志在我心底盤據著。「二律背反」這個我至今深信不疑的宇宙定理也毫不例外地在我身上應驗——我生來容易心軟,正因為這樣,我的行為反而加倍地心狠手辣了。我作了一件殘忍的事——我抓起了這兩隻生欲死、忘了飛翔的鳳蝶,然後,你猜我作了什麽事?我把這兩隻恐怕雷劈到頭上都分不開的蝶硬生生拉開。本以為輕而易舉,偏偏無論如何都分不開,我於是使勁了力氣扯開他們,兩隻才分了開來。我把牠們放在鍵盤上,以為牠們大概會自己飛走吧,可是,沒想到牠們不但不離開,甚至益發陶醉似地,劇烈地抖動著小小的軀體和翅膀向對方靠近。你猜猜,我看見這種情景之後使了什麽手段?打死牠們?才不是。真正的凌虐不是執行死刑,而是執拗的拷問,這點我很清楚。我用兩分别抓起兩隻蝶,一隻往東、一隻往西,看準最遠的距離就朝空中高高地抛出去。啊啊!我的殘虐在這件事上算是極致了吧!你想必不會以為對這等弱小的生物施虐是可以容許的。現在你大概可以瞭解了吧,我這個人,我這個人實在是胡作非為,離經叛道的事樣樣幹得出來。如果你對我有任何看法的話,請特別留意這一點。你問我這兩隻蝶後來怎麽了?那當然是如癡如醉地在被抛出去的空間裡畫著好幾個同心圓打轉,勉強才能畫出方向不定的曲線;有時似乎快要墜地,卻又為了找尋被拆散的對方而拚命地飛了起來。然而,命運畢竟將牠們導向了漸行漸遠的結局,
各自都朝相反的方向尋覓著對方。接下來,突然地,兩隻鳳蝶幾乎同時像是從爛醉當中乍然醒來一樣,不再繞圈子,毅然朝相反的方向遠遠地飛走了。我想此後在這個無邊無際的空間裡,牠們應該再也沒有重聚的時候了。
蝴蝶的故事說得有些長了,雖然我還想告訴你那加倍熱烈的豬的故事、更狂野的牛的故事,還有更難言喻的蛇的故事,現在還是作罷了吧!如果你願意的話,我是可以把每一種生物部拿來說一說,比方說那隻蠶……,不,還是就此打住,回到正題上吧!我可以說的故事實在太多了,若要我把某一天某一分鐘內的所見所聞、所思所想全部鉅細靡遺地說出來,起碼要三個月的時間。我沒有那麼多餘裕,你想必也沒有那麼空閒,所以,光是想著該如何把這個已經起頭的故事簡潔地說完,就十足叫我心煩意亂了。
我嘮叨了這麼多無關緊要的小事,其實真正想說的還在後頭;在開始接下來的話題之前,是有必要先說說這些無關緊要的小事的。
二
剛剛也說過,我想戀愛,一心就盼著愛情而已,只有愛情是我唯一的熱切想望。對於我這樣的廢材來說,本來就沒有所謂理想或者希望那種體面的東西,因此我從來也半點沒考慮過什麽名譽、成功或富貴。我唯一的願望,是將自己喜歡的唯一一個女孩、自己所愛的唯一一位女性緊緊地擁在懷裡。是的,那是我全部的願望,一直到現在都不曾改變。啊啊,我所愛的女人啊!我要用盡我胳膊的力氣將她抱緊,貼著她甜美的唇,那麽,當這副身軀與她的肉體合而為一的時候,「我」才終於能夠展現出它完足無缺的容貌!你知道嗎,這個想法一旦在我心底冒了芽,立刻以驚人的速度抽長,不久就在五體〔註1〕當中紮了根。你相信嗎?這個世界不會有像我這樣的偏執狂了,我是真的瘋子,但這是我年少以來的夙願,雖然不值得自傲,也算求仁得仁了。至於我為何變成這樣的人,我想已經不需要多作說明,聰明的你從我剛剛說到的少年時代的環境就可以看出端倪。你覺得很荒唐嗎?可是就我看來,人類思想感情的萌生和發展總有一些荒誕無稽、不正經又瑣碎的事象作起頭,而這個重要得幾乎支配了這個人一輩子的瑣碎事象則必有千萬種可能、人人各不相同。這麼說的話,對於我從離經叛道的圈子裡淬鍊出一個足可謂我的血與肉的價值千鈞的思想來,也不用太大驚小怪,不是嗎?況且,所謂的離經叛道隨著時光推移,可能越來越不像離經叛道呢!
我想要一個愛人,帶著一種苦澀而癡狂的心情想望著。夜裡就寢的時候,我總是道一聲「愛人啊,睡吧!」才躺下的。她沒有名字,不能喚她的名字確實很遺憾,可是別說名字了,我連她在哪裡都不清楚,因為,你看,我與她一面也沒見過啊!有時半夜醒來,在我心底浮現的一定是愛人的面影。雖然我沒見過她,她卻真真切切地站在我的眼前,那恬靜地微笑著彷彿聖女般的姿容清清楚楚地映入我的眼簾。我以虔敬的心情閉上我的眼睛,因為愛人的姿容無比莊嚴,我看得見她的周圍為光所籠罩。我伸出雙手,緊緊地將她抱在懷裡。啊啊!我巨大的女性!我這世上的最愛!我熾烈地吻著我愛人的唇,我的唇熱情地索求著她。我將愛人的全副身體靠著我,胸膛像火燒一般,我對她滿溢的愛甚至使我流下淚來。
請原諒我不知不覺亢奮起來……此刻我的胸膛彷佛就要裂開,你應該也看到了我的筋肉像起痙攣似地抽搐著。在你面前,我才敢厚著臉皮說這些話;換作是别人,我是絕對不會說的,畢竟在别人面前,我絲毫不會有說這些事的心情。請聽我說,在你面前我一點都不在乎自己變成什麼樣子;聽好了,從前我不管遭受到多大的威脅,也不曾像今晚這樣將自己的原形曝露在他人面前,可是你,面善又純潔的你,請看進我的内心深處。我是一隻野獸。如果聖賢之道才是為人之道,我無疑是走上了歧路、活該被瞧不起的存在。你儘管輕蔑我吧,但是千萬別拿我當笑話!野獸可以被看輕,但絕不是應該被嘲笑的對象,畢竟它連值得你一笑的價值都沒有。提到這裡我有個想法,我想啊,如果這地上再次為野獸所據,該有多好啊!我不是期望人類滅絕,請你别動氣,我的意思是希望現在的人類把所有的生活樣式和文化全部忘掉,再一次回到野獸的狀態。說實在的,比如說當我看到那些花幾百圓買來不為保暖,而是掛在肩上給人看的圍脖就感到莫名的嫌惡。從它垂在背上而不是圍在脖子上就可以知道,它在最關鍵的禦寒上起不了任何功能。看見這情景你還能平心靜氣嗎?我簡直想吐。還有,比如那個收音機,這東西實在讓人受不了,不管你走在路上或是坐在室内,那個喋喋不休衝撞你耳膜的噪音是什麼東西!怎麼忍受得了!那東西沒讓人類集體瘋掉才真叫我覺得不可思議。我要是在這個城市裡再住上兩年,肯定要瘋的,這點我十分清楚,所以我打算再過一年,也就是趁我還没瘋的時候隱居到鄉下去。你說如果連鄉下都聽得見收音機沒日沒夜的播送怎麼辦?當然是搬家了。搬家之後還是一樣的話嗎?你乾脆說這世間都被收音機的聲音充滿的話怎麽辦好了,如果真變成那樣,我是一定會瘋的,只能想到這種結果了。另外,只要一想到那些市區電車、汽車和飛機,我就全身發毛。市區電車那種東西明明就像蛞蝓一樣慢吞吞地貼著地上爬,竟然一下撞車啦,一下又追撞啦,總是在出事,真是太糟糕了。你再想想看這傢伙肚子裡的東西──皺巴巴像醃過的酸梅一樣該進棺材的老太婆、一大早就慘白著臉大打瞌睡的中學生……其他的雜碎就不提了,說也說不完。至於汽車,這傢伙的劣行實在讓人不敢恭維―─路已經不寬了,開得那麼快,是要趕著去赴死嗎?迅風那樣──不,用迅風來形容那傢伙是抬舉它了,我要修正說是瘟疫──像瘟疫那樣,颼地掃過你的袖子和衣襬就走了,只留下塵土和不快。真是會讓人短命哪!還有,你說怎麼著,當你刻意閃開來站到路邊去的時候,它又發出尖銳的聲音突然煞車,從窗口探出頭來喊你一聲「大爺!」〔註2〕,遇到這種情形,再怎麼好脾氣的人也會氣得跺腳吧!再來是飛機,早上的新聞才說它飛越太平洋啦,横越大西洋啦,到了晚上準又有摔下來的消息,哪裡是什麼壯舉嘛!如此種種歸結起來,我更加覺得自己是個不適合生存的人了,真的,打從很久以前我便一點一點地感覺到自己是個不適合生存的人,只是連我自己也不曉得這種感覺會在什麼時候累積到那個會帶來恐怖破滅的極限,只怕就在不遠的將來吧!我的破滅可是和你一點關係也沒有,因為我自己根本也不在乎……
真抱歉,我又岔題了。好像變冷了啊!外頭大概在下雪吧。話說回來,今年反常地一場雪也沒下,明明後天就要迎接基督降生節〔註3〕了呀!對了對了,說到基督降生節,據說我是在節日前一天的大半夜出生的,所以明天可是我的生日哪!你問我幾歲了?啊啊,你問到了我的傷心事,明日午夜,我啊!我就滿三十;後天早上睜開眼,我已經不能不把自己的年齡算作三十一了。今天是我三十歲的最後一天,我差點忘了這件事,現在意外得知這個驚人的事實,我又是歡喜、又是傷心。三十歲!啊啊,我的青春就這麼一去不返了!就這麼消失了!我在這裡就此宣告它的終息。你十八歲是嗎?哦,你為什麼要告訴我呢?你大概想不到你的這一句話如何地刺痛、刨刮著我的胸口,但我要告訴你,你的這一句話已經對準我生命的要害扎進最後一刀。我的青春從此拉下最後的一幕,對我來說,青春不再的人生已經不算是人生了,當我還在你這個年紀的時候我就已經是這麼想的。我還沒把我十七、八歲時候的故事告訴你吧?我本來就想說這個故事的。且聽我娓娓道來。當年,我對戀愛十分憧憬,渴望有個戀人,連在睡夢中也不忘了祈求「我所愛的女子,現身吧!」這是我靈魂的呼喚。如果此時此刻她出現了,我已經準備好用盡我全身全靈的力氣將她擁抱,即使只有一分鐘的時間,不,只有一秒鐘的時間都好,只要在那一秒鐘我的肉體可以與戀人的肉體完全相融、我的靈魂可以與戀人的靈魂完整地契合,我已別無所求、別無所欲,只願「將此身瞬間化為無形」。直到現在,我仍然為了那一秒鐘等得心焦。從前我相信那一秒鐘會在我三十歲以前降臨到我的青春,並且深信不疑,可是如你所見,直到現下此刻它從來都不曾降臨。我對我自己發誓,如果到了三十歲結束的最後那一剎那我還無緣經歷那一秒鐘,我勢必要了結自己的生命、絕對不要再歹活下去。請不要笑!我也知道這聽起來很荒謬,但我只想說一件事,請讓我說吧!我要說,世間所有人,無一例外地正在被比我更愚蠢的念頭所糾纏,尤其在他們抛擲生命的瞬間,若不是愚蠢到了無可救藥的極限,他們是不可能斷然將生命抛卻的。你别誤解,我不是在責難他們,反而要為了這一點對他們心生景仰。如果他們不是那樣地一度岔離他們人生中的常規,我對他們絕不會有半點切膚之情。話再說回來,我的人生規劃就像剛才說的,即將迎向它大團圓的結局;我長久以來的各種演技都要變得空洞而無意義。我不相信在這僅剩的二十個鐘頭内,有可能出現讓它轉為充實而有意義的變化,因為根據那恐怖的蓋然性法則,那直須唾棄的慣性法則,連最小限度的可能性都不會給我。
青春方酣的你!在我精神的内部,就好像芬芳的酒正在變成讓人皺眉的醋酸一樣,我對這人世間的愛也經歷醱酵作用,逐漸變成強烈的憎恨。就算我的人生和青春在悠長的時劫當中幾乎無足輕重,相信我這無限小的憎恨必定會與無限小的憎恨一起對這宇宙施加破壞的作用。
三
話說如此,其實我也有過幾次戀愛的感覺,遇過一些像是可以成為我戀人的女子。回想起來應該是我中學四年級的晚秋。學校放學後我和朋友一如往常地到公園附近的一家餐館吃天婦羅―─我們倆天天到那裡吃天婦羅,從來沒間斷過,一天也沒有!當放學的鈴聲響徹校園的同時,只感覺到天婦羅的香氣一個勁地撲鼻而來,此時如果還有繼續講課的老師,朋友與我就會擠眉弄眼地在肚子裡吐惡言,終於等到起立敬禮完,一溜煙地往外衝。每一次最先衝出去的總是我。等不及老師答完禮,換句話說,老師的頭都還沒抬起來我就先動作,因此我也常常被罰重新敬禮,就是有這麼可惡的老師!我們跑回宿舍丢下書包,雙腳就自動朝賣天婦羅的店走。我和友人的步調不約而同地相當一致,從學校到天婦羅餐館走快些的話來回要三十分鐘,而門禁是五點,我們在校門前碰頭。
「喂,幾點了?」我問朋友。
「整四點半。」朋友說。
「好,走吧!」
大概就是這個樣子。如果離門禁只剩二十分鐘,我們就用跑的;如果連二十分鐘也不到,就只好放棄了,這種時候會採行別的手段——九點熄了燈,當大家都睡了之後,我們再爬牆出去。你知道嗎?夜裡的街道真的好美啊!有一回夜裡從天婦羅店回來的時候,被食古不化的漢文老師發現,託他向校長告的密,我們停學了一個禮拜。那一陣子好開心哪!因為我家就在同一條街上,每天從早到晚我們都是在天婦羅店渡過的。這世上的事就是這麽莫名其妙,為了不讓我們吃天婦羅而施加的處罰,卻反倒給了我吃天婦羅的自由。好笑不好笑?好笑的話,放聲大笑也好、隨你高興怎麽樣都好,笑一笑吧!你為什麽不笑呢?吃東西的故事沒意思?那真是可惜了,我還以為吃的話題無窮無盡,你想聽多少我都能說呢!
接著我就來說說我們是怎麽遇見那個彷彿可以作戀人的女子吧!事情經過是這樣的。那是一個週日,我們倆從早就在街上閒晃。我那朋友是個哲學家,對叔本華尤其傾倒,總認為這個世界令人悲觀和嘆息。我嗎?我根本沒在唸書,換句話說就是個廢材。當時,我那朋友自己說他正處於一個精神上的轉變期,他對我說 :
「我是何等一個傻子啊!從今以後我必不再論道哲學。」他援引了某個哲人的話來說明自己的心境,又說:
「哲學家如身在沃野,嘴嚼乾草。」說畢又補述一句:
「今天起,我要抛棄哲學,開始談戀愛。」
這就是他從哲學家到戀愛家的轉向聲明了。我因為從來没有什麼學問基礎,二話不說就應聲答道:「那好」,以表支持。朋友陰鬱的臉頓時開朗了,他一直是過著憂悒的日子,因此這個轉變使我大受刺激。我們十分快活,我們跳著華爾滋,那是從街上跳舞的地方偷看來的舞步。我們穿過落葉開始飄起的噴水池公園,朝著最熱鬧的街道走去。那條街上成排都是百貨公司一樣的大商店。我們倆穿著寒傖的制服昂首濶步,當我們來到一家和服店時,忽然見到兩三個女人,還有那個女子正在裡頭買東西。最先發現的人當然是輕佻的我,我那朋友雖然不再當哲學家了,長久以來已經養成了走路只看地面的習慣,好吧!就算他沒盯著地上,美麗的女人也很難清楚地映照進他掛著眼鏡的眼底。我輕輕地碰了一下他的手臂,什麼話也沒說,什麽話也說不出來,因為怕一開口就會被那幾個女人發覺。朋友馬上注意到了,他輕輕笑了一下,突然低聲喊道:
「機會來了!」
我立刻明白了他的意思。我們在路邊的樹蔭底下停住腳,經過五分鐘的商議之後,斷然決定主動出擊。我打前鋒,意氣揚揚地走進和服店,掌櫃的疑神疑鬼地看了我一眼。啊啊!穿制服的中學生為什麼會被人那樣看輕,我到現在仍覺得難以理解。那些店員連一聲「請進」也沒說,但是這也沒什麼大不了的,我們只覺得走進一家女人才會駐足的店有些難為情而已。那幾個女人都回過頭來了,哦!那當中的一個!穿著淡紅色衣裳、年紀不過十八歲的女性!她正是我們夢想中的故事女主角,當我從正面一眼看到她的臉,我便清楚地感覺到了。她有著無比柔美的腰和一雙美麗的腳,我的熱情頓時沸騰到了極點。啊啊!穿制服的十七歲中學生真是可悲啊!
不久,她們走出和服店,我們也跟著走了出去。我們始終隔著十步左右的距離尾随在後,她們走到哪裡便跟到哪裡,就像兩隻忠實的狗。寒風拂掃過街,街道兩旁的路樹窸窸窣窣地打戰,悄然無聲地落下葉來;落葉隨風舞動了一陣之後,留下淡淡的回音躺在地上,我一路諦聽著自己的心跳,以及大自然所交織出的這些似有若無的聲響——完全不在我的預期之内。對於這個事實,你會不會也覺得很不可思議呢?就是人在最激動的時候,平常無知無覺的這些細微的聲響會在轉瞬之間變成天地間唯一存在的聲音,將我們轄治。
她們走進了一家飾品店。那是一間窄小的店舖,我們只好在隱約可以看見她們身影的樹蔭下等著她們出來。三位女子經過了頗長的時間之後,終於雙手各拎著滿滿的提袋走出了飾品店。那位美麗的女子站在她們中央一起往前走,然而只有那位美麗的人曾經兩度回過頭來看著我們。
我們已經恢復了平靜。她們從繁華的街道逐漸走到僻靜的小路,我們就這麼尾隨了大約半個小時,忽然在行人稀落、路旁成排的房子也將要走到盡頭的地方,她們不見了。就就那麼一眨眼的工夫憑空消失了。我的朋友氣得跺腳、拿下眼鏡來擦,但我看見了,我看見淡紅色的衣裳飄動,接著那美麗女子的臉匆匆地看了我們一眼。我告訴朋友我所見到的,他感動得幾乎要掉涙,因為他正好摘下眼鏡才錯過了我所看見的。他慌忙戴上眼鏡,偏偏沒戴好又掉了下來,我就在半空中將眼鏡接住了。我們倆商量過後再次採取行動。女子的家十分清幽,我們茫然地在門檻前呆立了好一段時間。
「有人在家嗎?」出聲的是我的朋友。沒有人應門,頗有進深的院落中傳出一些聲響。
「有人在家嗎?」我重覆朋友的話又喊了一聲,然後我們就像善盡了職責似地默默等著。彷佛聽見有人從裡頭走了出來。
「有何貴幹?」那是一個二十五歲前後、體形瘦削的年輕人。
「不,沒什麽事。」我答道。年輕人氣定神閒地走出來,站到我們身旁。他悠閒的神態令我們頓時覺得輕鬆起來。
「不,有事。」我的朋友馬上否定了我的回答。
「什麼事啊?」年輕人一邊笑著,一邊像是對舊識說話般詢問我們。
「呃,剛剛走進貴府的小姐……我想應該是走進貴府没錯……」朋友一本正經地說。
「喔,確實是進這個門,怎麼了?」
「沒,沒什麼。」我不必要地插嘴道。朋友沒理我,繼續問:
「請問,小姐已經出嫁了嗎?」
年輕人放聲大笑起來。
「不,還沒出嫁,但是明天要嫁人了。你們應該也看到了,今天就是出門去辦嫁妝的,那是我妹妹。」
我們就這麼碰壁了。稍頃,朋友怪聲怪氣地說:
「喔,這様啊!」又壓低了聲音對我說:「喂,回去吧!」我輕輕點了點頭表示贊同,但因心中百感交集,於是忍不住開口道:
「令妹實在是個美人!」
年輕人開心地笑了起來。我一定臉紅了,趕緊跨過門檻走出門外。朋友還留在門裡說道:
「讓你見笑了。」
這時,年輕人加倍開心地笑著說:
「不,一點也不,你也不必在意。年輕時誰不如此?」
我們向年輕人鞠個躬便離開了。
啊啊!那位年輕人的和藹!還有,穿制服的兩個中學生的寒愴!
你知道嗎,這就是我的初戀,不覺得很可憐嗎?我們就在那場悲哀的戀愛首航當中全軍覆沒,之後大約一個月的時間裡,每日食不知味,陷入深淵般的憂愁。哲學家朋友的臉上總是帶著一副讓人不忍直視的悒鬱神情,但我們一直咬著牙忍耐著這番考驗,絕口不提我們共同的失戀。
四
那是我五年級的時候。當時我十八歲了,因為暑假回到家裡。季節進入八月下旬,暑假也快結束了,陽光已經變得柔和,路樹也再度窸窸速速地打戰起來;街道上起風了,天空在樹頂上逐漸拔高。寺院的鐘聲想必是從以前就存在了,但在那時才第一次傳進我的耳朵,因為大自然所交織成似有若無的音響已經在我心中復甦。我開始準備回學校上課了。
在這段期間裡的某一天,住在隔鄰的我的一個兒時玩伴家裡有同學來訪。她向我介紹了她的同學。晚餐過後,她們一起來到我家,我們就在我的書房裡天南地北地聊。我的靈魂被那位同學所吸引,完全地著迷,十二萬分地愛上了這位女孩,我的言談因此逐漸變得語無倫次。我的兒時玩伴察覺到我的不對勁,慌慌張張地對同學說要回家。她們走出了我的房間,離開之前,我的兒時玩伴就當著那女孩的面輕輕地抱了我一下。這對我們來說絲毫不是不自然的舉動,但我生氣了,非常地氣憤。
由於氣憤,我喜歡的那位女孩第二天要離開時,我仍然鬧著脾氣,也沒去送她。多傻啊!那樣打動我心扉的女孩就要離開了,我竟然還躺在床上,真是太糊塗了!
我後悔了。極度的悔恨包圍了我,但幸運的是,我知道女孩的住處,這總算使我得到些許安慰。
回學校之後又過了兩個月時間,這段時間之内我不斷地想念那位女孩,在心底描摹著她的身影,一時半刻也未曾稍忘。進入十一月,在一個吹著寂寥的風的週日,我終於下定決心對誰也沒提地前往她的家。我搭上了火車,一個小時後下車的地方是一個冷清的鄉村小站。為了壓抑我胸口的悸動,我在車站出口站了片刻,欣賞那裡的田園風光。啊啊!這就是她眼中所見的風景!這裡就是她上下車的車站哪!——那實在是很溫馨的聯想。你能瞭解嗎?人之所欲其實都是很微薄的小事,我也沒有過分的野心;只要能與她在一起,我情願永住在那寂寥得令人感傷的田園。我邁步上前,很快就找著了她的家,雖然心裡還有一些躊躕,但又想到既然都來到了朝夕戀慕的女孩家門口,若就此回頭,還不如一死來得痛快。因此,我鼓起勇氣敲了她的家門。一位四十歲左右、氣質優雅的女人為我開了門。
「請問,您是哪位?」
我報上自己的姓名,那位女人沒有半點驚訝的神色,只說:「那請進吧!」我進了屋子,與那位女人相對而坐。
我先開口說:「我是為了令媛,對您有事相求而來的。」
「我聽小女提過你,有什麽事請直說吧!」
我戀人的母親出乎意料地以親切的言辭待我。那想必是因為我囁囁嚅嚅的緣故,她才這麼作好使我舒心。我欲言又止,預先計畫好的種種臺詞一齊湧上了喉頭,刹時為了該取捨哪一個臺詞而迷惘了。各式各樣的臺詞在我的聲帶底下推推搡搡、鬱塞不已,這個時候我才發現這些臺詞全都派不上用處。我感到困惑,這時突然有一個全新的臺詞從心底冒了出來,這句臺詞以千鈞萬馬的聲勢力排所有推推搡搡中的臺詞,從聲帶的深處跳了出來。
「伯母,請把令媛嫁給我吧!」
不是我講出了這句話,是這句話憑著自己的聲勢迸發出來的。然而,這話說得太好、說得太漂亮了!直到現今,我仍然認為它是我有生以來說過的最擲地有聲的一句話,僅管它很不幸地並未奏效。
伯母以低沉的聲音回答我:
「說來實在遺憾,她在故鄉已經有婚約了。承蒙你看上小女,我由衷感謝,但這件事情恐怕沒辦法答應你了;更何況她父親大約一週前剛過逝,我們不久就要回家鄉去了。」
也許是我的主觀,伯母的聲音聽來有些黯然。我很訝異會聽到她父親的死,當我的視線朝隔壁房間望去時,我看到簇新的白布覆蓋著遺骨壺、線香的煙靜静地裊裊而上。突然地,我感到悲傷,於是說道:
「令尊去世了嗎?我不知道這件事,請讓我也上個香吧!」
這時候,從餐室的紙門之間出現了穿著女校制服的女孩身影。啊啊!那正是我在夢中也描摩著、思念著她姿容的戀人。她以含笑的眼眸看著我,很快地又失去蹤影,這是為了不讓她母親發現的緣故。我的心跳加快,但我不得不隨著她的母親站起、往隔壁的房間走去。她的母親為我點了香,我便恭恭敬敬地在亡者的靈前磕頭、久久地伏著,突然感到兩行熱淚從我的臉頰流了下來。我忍不住用手抹去,手背上便留下了一道從手腕到食指尖的水痕。啊啊!我是哭了嗎?不,我沒哭,只是胸口上有著沉甸甸的壓力,那沉重的東西直壓在我的心上使我招架不住而已。我站了起來,回到會客的房間抓起了我的帽子——那是一頂陳舊又有破洞的帽子、一頂壓扁了的、別著金屬徽章〔註4〕的帽子。
「打擾了。伯母,再見!」我朝著門快步走去。吃驚的伯母跟在我後頭追了上來,我目不斜視地跑出門後回望了一眼,在走下脫鞋玄關的伯母背後看見了她的臉。
「再見了,伯母!」我再度喊了一次,然而對方大概是聽不到的——只有我以為是自己喊了,其實從未發出聲音來。
好心的你啊!這就是我的愛情了,我的愛情就到此為止。從那時起,我再也沒遇見過她。那之後大約過了四個月我就從學校畢業了。她應該也從女校畢業了,因為她的同年級同學,也就是我的兒時玩伴也畢業了。四月底的時候,我從隔壁的兒時玩伴口中得知她與母親一起回去了遙遠的故鄉。故事就這麼結束了。時間一點一點地將她的身影從我胸口抹去,我也逐漸淡忘了。兩年後,當我又聽說她結婚的消息時,已經感覺不到任何衝擊。她已經結婚的這件事,是從隔壁女孩與我母親的閒聊當中察覺出來的。
你覺得她後來過得如何呢?我並不清楚。然而奇異的是,自從我再無法見她的第四年的某一天,我收到了她的來信。信上只有署名,沒有地址。直到現在我還能覆誦這封信的內容。
與君一別,倏忽四年。分袂以來,思君之情,無時或釋,憂愁不減反增。此番心情,吾久秘不欲人知。嗟夫,關河迢遞,雲程阻隔。縱思君情殷,亦絕無相會之期。每憶當時别離情景,猶覺心痛欲裂。餘生惘惘,所記憶者,惟此時此刻耳。然當時怯懦,未能一吐衷言。及今思之,悶悶於胸,此恨當終生難消。如今舊話重提,非為抱怨,惟自傷年華消逝。憶昔相遇於君家,初次會晤,已暗自傾心;無奈身不由己,終難啟齒。吾乃一介女流,顏然無力,徒倍覺思君,歷歷在目。
別了!別了!君值盛年,願兄忘懷,莫再以妹為念。修此寸箋,唯此願而已。別了!
這就是她信裡的内容了。我那槁木死灰般的心幾乎要為此重新燃燒,可是,一
一切又在沉睡當中淡淡地結束了。
從那之後又經過了多少星霜啊?到如今,對她的所有回憶以及我的青春時光早已經消逝失蹤。
尚在青春年華的你啊,我對你說的就是以往至今我所有的愛情了。無可否認,我確實是個乏味的人,然而對於一個像我這樣深深地渴望著愛情、熱烈地想要一位戀人的人,神竟然連一秒鐘的愛情都不曾施捨給我,叫我無論如何難以接受。啊啊!青春正在消逝!它正快速地離我而去!
好心的你,耐著性子聽完我又長又乏味的故事的你,天似乎快要亮了。把那件上衣遞給我吧,我必需趁天未亮趕回家去,因為公司的出勤時間是七點,何況我還得搭上那個溫吞的市區電車,搖搖晃晃將近一個小時先回家收拾準備不可。好,好,有緣的話未必不會再見。第一次到你這裡來就對你說這些故事,你一定覺得我不是什麼正當男人吧,但如果我告訴你,我是連一個可以說這些話的朋友也沒有,你一定多少可以原諒我的失態吧。你想必曾經聽幾十個,不,幾百個男人講過同樣的故事吧,但是像我這樣意志與行為極端分裂的男人,應該還是第一次遇到吧。啊啊!我就這麼在你身旁躺了一晚。我是多麼地想要把你抱緊,卻作不到;我一點都不因此自豪,反而覺得羞慚——像我這樣窩囊的人只有被瞧不起,才算人符其名吧。
啊啊!我好想抱著你!用這兩條手臂所有的力氣將你抱緊!不,我沒這勇氣。啊!不行!不行!把我的帽子拿來吧!下次來的時候再看看吧!屆時,我一定也拿出勇氣給你看的。現在不行!許多想說的故事還充塞在我的胸口,實在不行。如果還有再來的時候,一定再說給你聽,現在,我的心裡還很難過……。咦,你,哭了嗎?怎麼了?到底怎麼了呢?別哭了,就當為了讓我心裡好過一點吧,請你別哭了。你一哭,下次來找你會使我的心情沉重,舉步維艱。好善良的你,請你别哭!如果在我下次到來之前,你願意認真考慮你與我的命運,那麽我答應你我一定會再來的。
天亮了,我得趕快走了。請你送我到那邊門口吧!真抱歉!善良的你,讓我看一眼你的笑容吧!謝謝你,這下我可以放心走了。再見!再見!
註1——五體指身體的五個部分,佛教裡指的是頭和雙手、雙腳,中醫指筋、脈、肉、皮、骨,也有一説是頭、頸、胸、手、足,不管依循的是哪一種分類,「五體」在一般文脈裡皆意指整體、全身。
註2——這裡說的應該是攬客的計程車。計程車自一九二〇年代起已經蔚為現代都會的風俗之一,當時東京市内流行起一塊錢可以搭到市内任何地方的計程車,日語稱「円タク」,可見通俗之一斑。
註3——原文為「基督降誕祭」,即聖誕節。
註4——有著金屬徽章的帽子是中學的制服,在文學作品中常作為學生的換喻。在高等教育人口稀少的年代,制服是另一種身分印記,因此提到制服(尤其是名校的制服,例如以「鑲白線的帽子」代表當時首屈一指的第一高等學校和學生)便能直接聯屬到與學校和知識分子有關的所有意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