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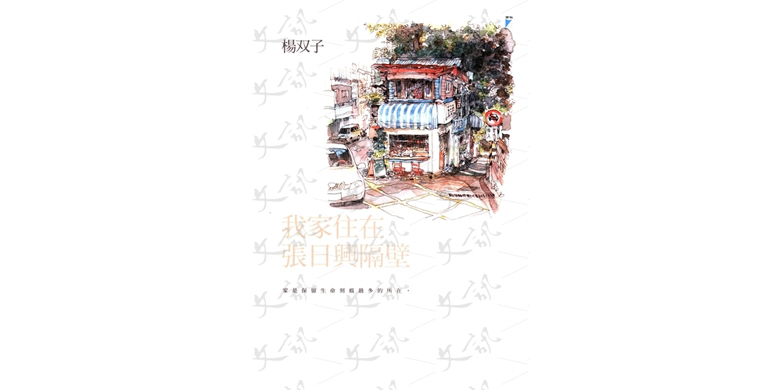
楊双子童年時期,家住台中烏日,成功嶺山腳下。曾經很長的歲月,男生考上大學後,開學前暑假都得在成功嶺接受短期軍事訓練,高唱「國旗在飛揚,聲威浩壯,我們在成功嶺上」。彼時的成功嶺,軍歌答數聲相聞,假日懇親大會車水馬龍,宛如市集,直到日後因為國家政策轉變,人氣寥落車馬稀,這時的楊双子,不禁好奇自問:「烏日,成功嶺,我們村子,我們家,以前是什麼樣子?」
「這裡,那裡,以前是什麼樣子?」簡單的一個問句,一點好奇,卻是系列追問的開始。楊双子往前追索,透過文獻、訪談,得知還沒有成功眷村,成功嶺還不是陸軍新兵訓練中心,百年之前的地區歷史。這段前因後果,記述於《我家住在張日興隔壁》列於卷首的同名單篇。這篇不但是全書起點,篇中此問也可視為楊双子以歷史為題材的寫作起點。從「後來一切都散了」「時間到,一切便又散了」的喟嘆,到「以前是什麼樣子?」的探問,層層溯源,向青草更青處漫溯,像歷史學家或刑警探員,渴求重建現場。歷史元素成為楊双子此後小說寫作的軸心。
若再加上〈你妹妹是虎爺接走的〉等篇,更可看出,楊双子的歷史小說,考據紮實,日治時期少女的生活面貌、情感思緒,也栩栩如生,這份田野調查的能力養成,並非全拜學術訓練所賜,有時與生活際遇、命運流轉相關。《我家住在張日興隔壁》書中多篇記述或有心栽花,或無心插柳,所形成的花開樹蔭。例如楊双子對虎爺瞭若指掌,已足以作為題材撰寫長篇小說,然此並非就讀研究所學術鑽研所得,而是緣於妹妹癌逝後,楊双子遇活佛師父,一句:「你妹妹是虎爺接走的」,促成她一步一腳印,百來間大小宮廟尋訪參拜之行。
《我家住在張日興隔壁》或可視為微型的作家養成史,其中幾篇都提到,楊双子為何又如何,從大眾文學汲取養分,以歷史百合小說重新接起台灣戰前本已有之的「少女小說」文類,突破文學主流路線框界,於小說界的藍海地帶奮勇馳騁。
楊双子最早寫的是言情小說——「孔子十五志學,我十有四而志於寫小說。」〈原來你這麼認真寫小說〉說的「寫小說」,指的就是長篇言情小說。言情小說寫作,是文學起步,也具有特別的個人意義:「寫言情小說聽起來是青春期少女圓一個作家夢的天真爛漫,於我是穿透陰霾裂隙的一束光,一絲垂入地獄底層的蜘蛛絲。」漫畫亦如是。〈汝讀書敢有讀閒仔冊遮爾認真!〉講述姊妹的漫畫嗜讀史。從學齡前到入小學後,從《小叮噹》看起,漫畫一本接一本,「我們是看漫畫學認字的。」國文造詣奠基於此,比同學認的字更多。國中後租書業興起,讀閒仔冊更加方便,漫畫、言情小說、金庸武俠,冊冊不放過,一頭栽進,全心投入,不捨晝夜,是家庭離散後,肉身飢餓、心靈荒蕪時的寄託。結尾說:「我們讀閒仔冊,不是逸樂,是求生啊。」全篇洋洋灑灑,主要在詮釋這句結語。
另外如打電動等娛樂,都表現出對次文化的熱愛,以上種種,點滴化為作品養分,因此,楊双子等新世代作家,近年崛起文壇,有個重要指標,讓向來不被看重、甚至落入保守派文人口實的大眾文學,獲得翻身的機會。作品不能因寫作手法面向大眾而被貶抑,也不因走純文學路線而自居高等。楊双子是有心人,書中告白:「小說到底是什麼?我問了再問,從大眾類型到嚴肅文學,一問十數年。」「出書前出書後,得獎前得獎後,無論寫的是言情小說、文學獎小說,乃至於純粹玩心的動漫二創同人小說,我一概認真無比。」
除了〈原來你這麼認真寫小說〉篇中交代寫作因緣,更值得注意的是,用語更鮮活、意涵更深層的〈文學少女的歷史異想〉。此篇藉由姊妹倆對話、辯論,細說歷史百合小說系列的發想、信念、展望與規畫,對話活潑風趣,相互鼓勵互相虧,文史知識融於對談中,長長篇幅一氣呵成,不煩不澀。在這些腦力激盪下,不但引領出「花開」雙書——長篇小說《花開時節》、短篇小說集《花開少女華麗島》,也以女性旅行的概念,預告了日後引發爭議的《台灣漫遊錄》之誕生。
雖然小說家在前序後跋,或訪談,或散文隨筆中,闡述創作理念,分享寫作因緣,是常有的事,但楊双子寫下此類文字,另外具有特別意思。2020年近尾聲之際,楊双子分獲《聯合文學》與《文訊》雜誌「2020年最受期待的青壯世代華文小說家」與「21世紀上升星座」的作家行列等肯定。儘管楊双子年紀不到四十,但說這是遲來的肯定亦不為過。之前的她,據自陳,14歲立志寫作,18歲出版第一本長篇小說,然而直到獲這兩項榮耀之前,「退稿字數累計超過一百萬,也因此長年認定自己是沒有天分的寫作者。」「始終無緣三大報文學獎,好書獎項亦擦肩而過。」
如今,被看見的不只是楊双子,而是寫百合小說的楊双子。楊双子細訴寫作來時路,讓讀者了解其寫作的堅持與理念,對志在寫作,尤其踩在非主流路線之上耕耘的作家,更具鼓舞作用。
相對於闔各言爾志的書寫發想,更能表現散文質地的文章,是幾篇傷逝追念的作品。與孿生妹妹生離死別的傷痛與不捨,30年來患難與共,互相鼓勵的追憶,不用形容詞,不須雕琢字句,僅以白描敘述,感情自在其中流動,令讀者悸動。
古稱三十年一世,這一世就是妹妹的一輩子。書中追念我們這30年。「我們」指的不是我們家、我們社區,而是我們姊妹。書中多用「我們」,而不是「我」,因為兩姊妹是既是雙胞胎,又是創作伙伴,自小一起生活,同甘共苦,即使念到研究所都同校,一輩子不曾分離逾七日,彼此是你泥中有我、我泥中有你的命運共同體。
因此「我們」一詞貫穿整本書。妹妹30歲癌逝,姊姊哀慟逾恆。本書主要內容寫姊妹情深、相知相惜、合作打拚的經過。〈我要煮飯給我妹妹吃〉敘述演講時被問及,如果妹妹復活一天,會如何度過這一天?「我想,必須是吃一頓吧。」吃飯,怎麼會是這件日常小事?「整個青春期我們都在肌餓中度過。」一前一後這兩句,把青春期如何節衣縮食,如何以精神食糧取代果腹糧食,細寫日常開支等細節,毫不煩瑣,反而緊扣著讀者的心,跟著緊張,怕她們斷炊。書中其餘以飲食、旅遊為主題的單篇,都難掩天人永隔的悵然。
《我家住在張日興隔壁》是記憶之書,是傷痕之書,是啟蒙成長之書,是至情至性、情理交融的佳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