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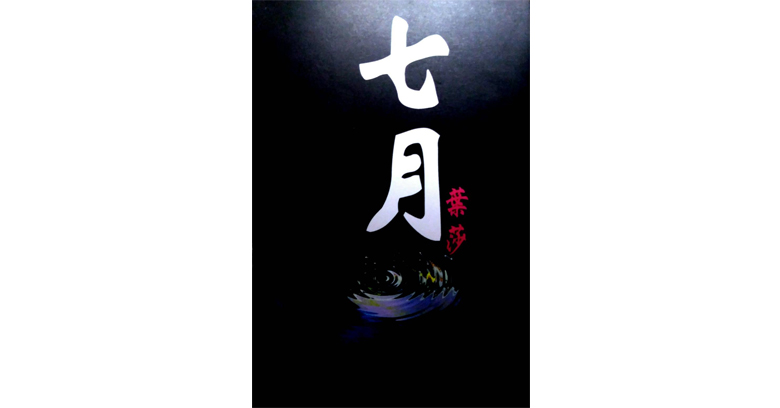
2022年元旦,我所閱讀的第一本詩集是葉莎的《七月》;冷涼的清晨開篇展讀〈鬼月第一天〉,亦頗難得讀詩有如是撼動的情境。
筆者寫詩筆快,讀詩目鈍,常於詩中上下推敲、往復讀誦研之,期盼在文學的玄旨神髓、意象經絡、聲色麗句之中有所神會,得材、得意或得句,內化自身創作資糧。創作體悟三十餘載有餘,鮮少評介他人之詩。現竟不揣譾陋,勉力為之;忝不量力,蓋因感動,當有記之。
翻開《七月》,詩人葉莎於蝴蝶頁親筆題詞:「發覺死神緩緩靠近/我才醒來」。人之忌憚,我無懼為詩;大抵詩之不凡,往往就是在常人無覺之情感幽微處抒發。扉葉之後,看見與台灣詩壇諸多交遊的新加坡詩人杜文賢(1960∼2019年)卡夫詩兄的序文;憶及詩人游鍫良家一面之雅—斯人已渺,而序文存焉—讀來心緒百感。
《七月》詩集,緣起於詩人追念結縭36年的先生骨癌離世(2017年3月6日),隔天竟是葉莎生日—常人稍具同情,即知情何以堪!何況筆者近年也陷入失恃失怙的境遇,更深知人生緣聚,自有難以言說復難以補填的情感空缺。
且看寫詩的女人,刀割為詩
早晨從一條水管開始/一拉長就噴出詩來//字詞葉大最愛微風/感情質嫩且害怕菌類/……一顆心耐旱也耐陰//時常蘭/時常蝴蝶─〈心之抗病〉
決定遠行/將自己打包送給天涯/據說那裏有詩團聚/字句微笑將憂傷隱喻─〈遠行〉
時常徘徊在文字的高緯度/啃咬自己……─〈視同鹿人〉
共枕人離世百日之後,葉莎調整好時空距離與心緒,著筆寫下了《七月》;試圖接通幽冥,連續30天,日日一詩(或一思),字句輕淺,卻銳如刀割,詩人若非清醒深知,便是過度痴傻—無法及人,惟能透過及物即事,追懷念想,像蘇軾〈江城子〉那樣「生死兩茫」與故人時空穿梭交會。詩中篇章意象輕描,反更深刻,以之鑑證:詩是活過、愛過的證據,對死的巨力之無可何如的抵抗;情深而痛—卻又甘受其反作用力。因之詩寫,乃成一種情感的療傷自癒。
復看種花的男人,替換詩骨
夜半時分/回到最愛的花園除草/鐮刀沙沙穿透玻璃─〈夜半時分〉
我看過那人分株春天/為愛換盆/……在遮光遮雨的棚下/碎裂蛇木混合假泥/……栽植的蝴蝶蘭/守著真誠的諾言/時間到了/就讓人看見想飛的臉─〈分株春天〉
詩人葉莎在詩作部分附記言及夫婿:這個男人相對內向、心地良善,喜歡在家養蘭蒔花、關照小小動物;從發現骨癌到辭世只有短短的11天,卻是詩人葉莎的半生追憶—若要忘懷,當是放其「流失」,而不是「留詩」!更不用在「走過田野時/採幾片紫花藿香薊/沿著不整狀鋸齒緣/為黃昏止血止痛」;也不用在死生割離之後還暗自承諾「浪會持續溫柔/像一切沒有發生過」。
詩旨華要
情深,不是呼天喊地的喧露;麥克風擴大的「孝女白琴」,「悲」乎?隱意而顯象,方得詩之情韻要旨。「意象」是詩人情思的有機偶合;葉莎值此人生遭逢—以「七月」追述,自有中國傳統習俗「人靈相通」的深切涵意。
雨停了,天黑了/有人從窗子進來/又從窗子出去─〈鬼月第一天〉
大廳無人或許有人/只見菩薩低眉/任空氣和寂靜互相推擠//我不留文字/獨看一朵盛開的蓮/想你愛花如此/昨夜應來看過─〈思念聚集〉
七月最後一日/麻雀和松鼠準時清醒/我穿衣吃飯讀書寫詩/聽見野牽牛大聲宣告別離/此後人和幽靈各自寧靜─〈素心如蘭〉
擺下宴席邀空入座/輕煙是唯一的信紙/寫上塵世的眼神//有人早退/不待揮別,急欲飄走/爐中一疊冥紙剛著火─〈邀空入座—第十五日〉
為求來生續緣/有人再次來到床前/襯衫上繡滿藍天/面孔漾著生前的笑靨─〈眼神忽略眼神〉
整本《七月》實難挑以句解;30首詩作,淡筆情深一以貫之,讀者自推自敲更有共鳴,太多劇透,反而傷了詩韻情緻。其實詩眼如花,擇節而破—《七月》以〈鬼月第一天〉開篇,詩人絕對「有意」把自己「附象」成一株不開花、嚶嚶而泣的緋寒櫻,由「泣、濕」直貫到《七月》最後一天〈花色漸褪的早晨〉—「寫詩的女人」已將巾被仔細拉平,讓陽光勻稱曬曝濕漉的殘夢,可以看出作者已知走出失偶情傷。首尾之詩對照,雖然還是灰暗「枯枝」,但寒櫻已換桃樹;輕綠更成緋紅—「喪偶」而不該「喪我」,「種花的男人」應會樂見「寫詩的女人」來年春天、院子更有生機顏色。
彌補幽冥與蒼天
世間情愛,不免有憾,但有詩記存情感履痕;《七月》之詩寫,文字所牽念之人雖隔一段時空距離,心情有了沉澱,生活亦多少拉回了常軌,雖諸多詩作不時暗藏「黑、夜、日落、暮色」字眼, 幸而仍有閃出「月光與星」,讓《七月》不顯陰森;反見光朗有情,有痛無懼。
詩之即離,拿捏不易。太離,便寡義冷淡,失之人溫情味;太即,則吶喊濫情、傷哀而淚眼。《七月》意象蜿蜒卻又坦然直面自己此生最深切的人事,可謂不即不離。其字句履淡,卻如X光穿透—膚面無血、筋骨有斷!而「生之斲傷」已披敷意象,如幽靜不喧的花蕊—以痛為瓣,靜靜開落⋯⋯。
筆者私以為,廣使年輕人喜愛的林婉瑜之諸多情詩新意書寫若屬豐饒、黠慧、釉光的「五月」,則葉莎之《七月》,更能見證其命運催逼之下滄桑、沖澹、昂然復垂熟的天成風韻。像「丈夫喝了一口酒出門,忘了回頭看妻子一眼」;像「妻子畫了一隻翅膀快要撐破空的鳥」;更如〈有一天〉:「我會永久保留/木麻黃曾經觸摸的天色/但願意遺忘/樹下如風的語言//深信此生是有翅的種子/無論飛過大河或是高山/有一天會和你突然相遇/並長成相似的樣子」。
死生縛纏,愛或哀或已難分。在「種花的男人」與「寫詩的女人」之間,當「種花的男人」靜靜地躺成也無風雨也無晴的「被詩寫的男人」;「寫詩的女人」終究也要「走至花園與蘭對望」,然後自己挺起,澹泊平和地站成「種花的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