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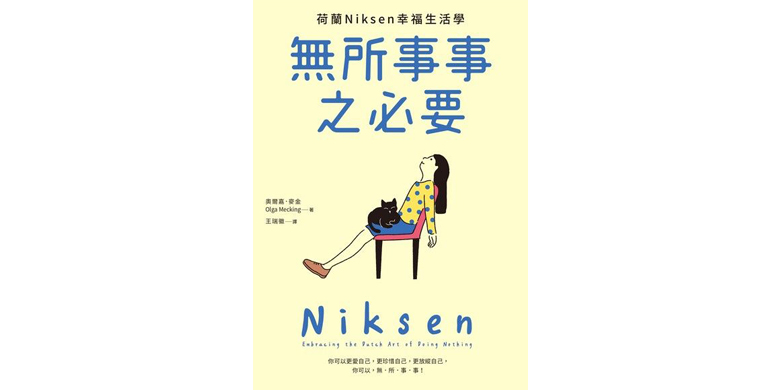
學會放鬆,而且不帶羞愧、不帶罪惡感,是人生最美好的藝術和慰藉。
——安東尼.塞爾登(Anthony Seldon)
《無所事事之必要──荷蘭Niksen幸福生活學》是翻譯時改動的書題,原名Niksen: Embracing the Dutch Art of Doing Nothing,按字面,可譯為「放空:擁抱荷蘭什麼都不做的藝術」。Niksen一詞源於荷蘭(較為準確的說法應是尼德蘭),近於中文的放空、耍廢、留白、閒散、無所事事,反映出了荷蘭特有的生活哲學,指不去做沒有特定目的、不具實際效益的事,而且心中不存批判。
作者奧爾嘉.麥金(Olga Mecking),出生波蘭,定居荷蘭,丈夫是德國人,麥金經常為英美報刊撰稿,此書的內容先發表在2019年的《紐約時報》,始料未及的是網友瘋傳而受到全球媒體關注,它搔著了這一代人的癢處,或者痛處。
麥金每天周旋於孩子、丈夫、家務、工作以及眾多親朋好友之間,如此日復一日的生活形態,我們其實早已司空見慣,乃至不覺得是問題。曾有學者表示,生病也有吸引力,因為可以理直氣壯地找回社會所認定的巨大惡習──什麼都不做。臥病在床,沒了健康而有權放空,更清楚地說,是被迫放空;身體無恙,可就不能「遊手好閒」。麥金說她想解決「如何能在履行一大堆義務和職責之外,挪出足夠時間來做Niksen」,也在想怎麼把Niksen具體導入公共和私人領域。
從傳統到現代,自西方到東方,辛勤勞作的價值取向一直位居主流,迄今,《伊索寓言》裡「螞蟻與蟋蟀」的故事仍是不少師長餵養孩子的雞湯,它的基調和「天道酬勤」的觀念相同,說誰「很閒」或「吃飽太閒」,話中就隱含了貶義,意味不做正事、沒盡義務。「志」就這麼一代一代「勵」得不遺餘力,至死方休。南韓的金江美40歲的時候,為找回自我而辭去工作,之後遇到一位曾在職場並肩作戰的前輩,聽說她已改行畫畫、寫文章,偶爾兼差接案,脫口而出:「沒想到妳是這樣生活!」嘲弄的口吻頓時使金江美心裡有不求上進的罪惡感。然而若置身丹麥,可能反而得到「棲息於自身」的極致讚美,意謂能「用自己原有的樣子快樂生活」,對人生價值的認定竟然差距那麼大,卡夫卡的提問仍然值得深思:「單單勤勞是不夠的,螞蟻也非常勤勞。你在勤勞些什麼呢?」
麥金想為喘不過氣的生活找出路,就開始探索荷蘭人說的Niksen究竟是什麼,並試著實踐,她的種種心得引起了廣大迴響,說明這不是她獨有的困擾。現代人擁有那麼多節省人力、時間的裝置,為什麼人卻愈來愈疲憊,閒暇愈來愈少?日新月異的科技產品,尤其各種電子裝置,更加速模糊了工作與休閒的界限。以美國為代表的現代化社會,忙碌卻儼然成了成功、優越的身分象徵,難道這也是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結合下的必然結果?
台灣人「壓力山大」,可以見諸孩童的功課表、聯絡簿以及成年人的行事曆與待辦清單,負荷早已嚴重超載。鄰近的日本、南韓以及對岸,狀況更是有過之而無不及。忙碌和壓力除了來自學校與職場,也不乏源於私人場域的,這是寄生於優勝劣敗世界裡的必要之惡嗎?東亞社會,特別是所謂的「儒教文化圈」,年輕世代因此普遍不願結婚、生子,出現了低物慾、不奮鬥的佛系現象,韓裔瑞士學者韓炳哲曾寫了一本《倦怠社會》去剖析。不少年輕人覺得大部分人生如果這麼爆肝、積勞,不如捐棄大抱負,但求小確幸。老一輩的眼裡,也許認為消極,反過來想,努力不懈地追求世俗成功,可能終究是另類的虛無與浪擲。
中國大陸近年甚至出現了「躺平主義」,他們的科技業流行「九九六」的工作模式──早九晚九,每周六天。馬雲對年輕人說:「如果你年輕的時候不九九六,你什麼時候可以九九六?」宣稱:「九九六是修來的福報。」結論是:「我們不缺八小時上班很舒服的人。」不僅阿里巴巴,華為、京東、拼多多、字節跳動等也都屢被形容為血汗公司,建立了功績社會的新奴隸制度。諷刺的是,馬雲某次接受韓國節目的採訪,透露自己後悔終日埋頭工作,沒時間陪伴家人,並稱若有來生,絕不會再選擇那樣的生活。「溫拿」咋說都行,「魯蛇」若不甘做社畜,似乎只好自己躺平,吶喊著:「躺平就不會再跌倒了。」
「躺平」這種打不過、躲得過的行動控訴,自然無法根絕問題。麥金在書後附了一篇〈Niksen客宣言〉,其中說道:「Niksen不該只是個人的責任,我們希望得到國家、城市、社會和社區的支持。我們想要更平等的分工,好讓每個人都能得到自己的Niksen時間。我們希望各種無形的、被忽略或低估的勞動形式能夠得到重視,而這些通常是由弱勢族群承擔。」換言之,Niksen必須是公民社會的共識。荷蘭社會開放、坦率、自由、平等,是個人主義的國度,加上強大的支持系統和社會網絡彌補了個人主義的各種挑戰,因此孕育了適合生活的人文環境。那裡,Niksen固然不是人人採行,然而重要的是──「他們生活在一個只要他們願意,絕對可以臉不紅氣不喘地進行Niksen的國家」。從台灣移民荷蘭的丘彥明在《在荷蘭過日子》書裡也曾見證荷蘭是個「以人道主義為出發點建設的國家」,其「尊重共生的精神,潛藏於百姓最基本的生活行徑之中」。
如果從荷蘭往北方的鄰近國家去探索,丹麥也有個特別的詞──Hygge,同樣不好對譯,大意是「處於愉悅的幸福感與安全感之中,心態輕鬆且開懷享受當下所有令人愉快的小事」。同類的字眼,瑞典也有,一是Mysa,動詞,指與人共度愉悅的時光,有幾分像中國北方人說的「凝聚凝聚」,其形容詞是Mysig,指環境或與人相處的舒適愜意;瑞典還有另一個詞Lagom,意思是拿捏平衡,強調「剛好最好」,近於我們所謂的「中庸之道」。芬蘭呢?有Kalsarikänni,相當於英文的Pantsdrunk,指「宅在家裡,穿著內衣,酒喝到酣」的一種放鬆狀態,芬蘭政府還特別在官網上做了介紹。挪威生活的關鍵詞Friluftsliv則從屋裡走到了戶外,它源自易卜生(Henrik Ibsen)的文學作品,字面相當於英文的free air life,指「徜徉大自然」,讓心靈得以從忙碌生活中洗滌、解放,這有如《莊子.齊物論》「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為一」的返本體驗。從Niksen到Hygge、Mysa、Lagom、Kalsarikänni,這些抽象概念能夠充分落實在具體生活,除了基於個人認同,也有賴與之相應的社會福利制度、務實的文化精神、有效率的政府運作。
論生活風格,我們台灣的代表詞彙是什麼呢?
《小王子》裡有句話:「真正重要的東西,只用眼睛是看不見的。」政府的異國考察,除了針對看得見的硬體,也得留心那看不見的文化肌理。對個別的讀者來說,不妨脫離既有的、早已視為理所當然的觀念框架,從字裡行間遊走到地球的另一邊,在閒逛中自我啟蒙,在超越中棲息於自身。